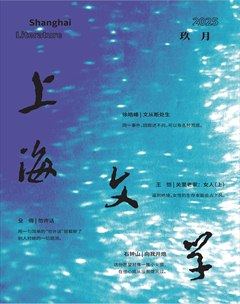一
人的一生,山等在那里。
一百年,于人是漫长的旅程,于山只是一夕。
进入天目山,宛如进入树的王国、草木的宫殿、美与自然的庇护所。或许,我们真正进入的是植物草木之外的时空。在山上,人会遗忘时间的存在。烂柯山上看仙人弈棋的樵夫,斧柄脱落全然不知,时间流逝浑然不觉。人们看山,到底看到什么?见仁见智。
天目山的护林员沈师傅与童师傅,吃住都在这山上,每月只允许离开四次。他们中哪一位是五十六,哪一位是五十三?问过又忘了。
在山上,没有一只鸟会过问人的年龄。而他们,作为山林的漫游者与守护人,与草木为邻、为密友,朋友圈里尽是枫香、银杏、柳杉、白鹇、黑麂、野猪,所听最多是鸟声,所说最多为喃喃自语。衣着装饰皆为草木色,多年来致力于学习隐身术,以被动植物引为同类而骄傲。
冬月某日,沈师傅在前头引路,童师傅垫后,我们一行四人由红庙出发,前往海拔七百米高处的瞭望塔看山。
谈及四时山林何时最美,沈师傅说,“十一月二十日最好看!”语气中含着不可辩驳的果决与断然,这让我们不免惊诧。
问他为何认定是那一日,而不是前后左右中随意生成的某一日。
“就那一天最好看。”他颇为孩子气地解释道,“因为树叶都黄了,然后又红了……”
边上弥勒佛似的童师傅却笑而不语,似乎在说,都好看呀,山上哪一天都好看的。
不及多语,我们的身体已落入密林深处,好似有一条隐秘通道,它是通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人们以身体触碰,进入其中。而被我们触碰的大概是一棵枫香树、一棵麻栗树,或许还有一棵槭树。
于是,“芝麻开门”——林间之门轰然开启,目之所及,高处的树枝与低处的落叶,经纬交织,纷繁、浩荡,扑面而来。枝上新旧交替,地上落满错综复杂的时间的絮语;新叶老叶,掉得满坑满谷都是。枫香树的叶子、麻栗树的叶子、槭树的叶子,心形、鸡爪形、锯齿状,卷着边角,干燥、薄脆,好似被抽干了水分的脆饼。没有风,落叶成了山林的主人,嚓嚓,吱啦,沙沙……被重力压碎的声响,彼此挤压发出的嘎吱声,以及人在行走时带出的簌簌声,我的耳边从未同时涌现如此多的声响。
落叶给人眩晕感,就像雪地和爱情带给人的。一棵树在它的一生中,到底会长出多少片叶子?无人知晓。美国诗人,博物学家安妮·迪拉德居然在《听客溪的朝圣》一书里写道,“一棵大榆树光是一个季节里就可能制造出六百万片树叶,全都十分繁复,却不费吹灰之力;我连一片也制造不出来”——真想知道作者所说的六百万片树叶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这世上有一些奇异树,能同时长出两种或三种截然不同的叶片,好像它们体内还长着别的树。它们是海南的赤桉树与西域的胡杨树。天目山上有没有这样的树?或许是有的。我们拄着树枝做的拐杖,走在落叶之海里,双脚发飘,身体晃荡,随时可能跌倒在地。落叶在离开枝头后,看似进入永久的沉睡状态,实则跨入下一轮物质循环中。大幕拉开,一系列氧化、分解动作悄然展开,落叶不仅能增强土壤肥力,还能抵抗全球变暖。
“随便什么时候,只要到荒野去,我们就不会空手而回。”当我手里捏着一片黄绿夹杂的枫香树的叶子,忽然想起此话。此刻,我被它错综复杂的纹理迷住了,好像是由心灵手巧之人一针一线刺绣出来,只有怀着巨大热情和生命能量的人才能做到。
天目山上到处都是这样的造物。你要细细打量,最好是“反复看”——这是古希腊人对敬意的定义。当你“反复看”,低处的细节被放大,高处的细节俯身而下,与你的目光接壤,与你的心灵相通。
毛蕨,蕨类家族最素朴的成员,叶片呈披针形,遵循古典的对称率。它们从《诗经》里走来,其形其叶天然地召唤出古老、永恒、灿烂等词语。
榧树,矮小的树。每长一寸都如此艰难。它以光为媒,需站在光线最多的地方——向阳坡地上,才能完成蜕变。条形叶片,好像缀着无数根闪亮的绿针。第一年出絮,第二年开花结果,至第三年才功德圆满。如此漫长,简直在锤炼观看者与种植者的耐性。
还有短萼黄连、鹅掌楸、白芨、五节芒、麦冬,呈卵形、针形、纺锤形,一一对应现实之物的造型。物种的多样与细节布局的幽微和神秘,让人惊叹。
置身林间,恍惚感袭来。看到土壤里的虫壳、腐木上的菌类,看到翅膀、蛛丝、虫卵,听到鸟鸣、水声、林中动物的移动声,感受林间跳跃的光斑、红眼睛太阳的热气以及土地的冷硬与霜冻。在山林,万物皆有连结和呼应,但这些呼应和连结非双眼所能窥见,亦非双手所能轻易触及。
幸亏,电子信息时代,人认识万物多了有力助手。识别植物的有“形色”,观鸟的有“懂鸟”——输入鸟图或鸟音,即可与全世界一万多种鸟类相遇。只认识一种鸟的人与认识一万种鸟的人,有何不同呢?是不是后者的耳边常有自然的旋律奏响?
童师傅告诉我,他的工作内容之一,便是将鸟鸣声上传至“鸟类监测”平台,时长不少于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