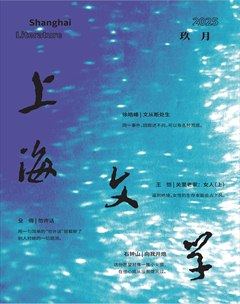十一月中旬上海的午后,晴日的阳光也是打了折扣的,仿若罩了一层磨砂玻璃,不像温哥华,太阳一睁眼,出门就得戴上墨镜。我仰头朝常德公寓六楼不确定的窗口望去,恍然看见七十八年前上海萎靡的夕阳里,她站在六楼的阳台,看远处高楼周边一大块胭脂红,竟是元宵的月亮,遂想到了自己身处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天地月刊》第十九期刊登的张爱玲散文《我看苏青》里面的一段话,张爱玲所谓的上海的“边疆”说的是外滩。那时她的阳台是望得见外滩的,不像现在高楼林立,早就遮挡了上海的“边疆”。那一刻,我站在常德公寓门口仰望那主人早已不在的六楼阳台和来来往往的行人,一阵晕眩袭来,脑海里瞬息闪回二十二年前卖掉上海的住房、在派出所看着民警在我的户口簿上狠狠地敲一个“注销”印章,连同身份证一道收走的镜头,连个作废的户口簿也没留给我做个纪念。如今短暂回到在异邦心心念念的城,不过是个匆匆访客,而我熟悉和喜欢的上海话,在上海竟也不是碰到谁都能讲的,遇到生人总是先要用普通话试探,而不敢直言沪语。即便跟自己的胞妹,也不方便讲上海话,毕竟她是跟了支内的父母在北方长大的,以后嫁了人,跟着做生意的丈夫开公司开到上海来的。我离开的那年,恰逢她搬来上海。虽是同胞手足,但童年有别,更有长在童年骨肉里的母语不同,也就有着不同的身世感。一个人童年的记忆总是冥顽不化,从不肯轻易在以后的人生里退场,时不时要插进一脚。眼前蓦然叠印出张爱玲黯然离开上海的情形……
那个情形,网上流传着真真假假的段子,靠谱的记载应该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中的那段:“一九五○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大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张爱玲离开大陆是此后的两年。出走的原因是错综的,但那次她难得没有推辞官方邀请,并精心打扮出席大会,却不料自己在那蓝灰色海洋里显出的突兀,这在她心理上不会没有冲击,毕竟那场景里的突兀并不是一种风头,而是陷她于边缘。
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旗袍的命尚未被革掉,我看到我母亲那时的黑白旧照,就有穿着旗袍的。不过那样正式的官方场合,新中国的第一届大都市的文代会,与会者多是要表现出合乎新社会正统审美的庄重感和严肃性,便要收敛起个性的穿戴喜好。从那统一蓝灰的集体氛围里,敏感自傲的张爱玲如何能不意识到自己与时代、与社会现状的格格不入?而她又不肯“委屈求全”放下个性的自我,即使只是换一件她不喜欢的衣裳。女人对穿着的个性坚持,最见得不肯屈从的内心。
一九五一年春她与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会面,弟弟问她对未来作何打算,她良久沉默后似乎答非所问:“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当然,事情不是换一件衣裳那么简单,她是预感到了比换衣更大更难以接受的改变。张爱玲是提早想到了。
当年上海一成“孤岛”,文艺园地便沦为国共两党都管不着的空档。张爱玲恰出头于此空档,遂被瞩目为奇葩,一夜风靡上海滩。木心曾在悼张爱玲一文《飘零的隐士》里曰:“而文艺是什么东西呢,文艺是哪里没有人管哪里就有文艺,如果既没有人管又有天才降生,那就是‘文艺复兴’,如果虽然没有人管却实在也不出半个天才,那就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一阵子,完。”张爱玲从小就被管怕了,一心想要做自己的主人。
柯灵提到张爱玲那次出席会议显得很突出的穿着,已经是“由绚烂归于平淡”,显然是对照张爱玲以往的“奇装异服”而言。年轻的张爱玲是喜欢引人注目的,至于她晚年的避世和极致简陋的生活,完全是上海时期她自我的彻底悖论,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在此文赘述。回到还在上海的张爱玲,她清楚自己没有颜值的资本,便在装扮上刻意另类,同时也有对童年那件来自继母的“碎牛肉颜色”旧棉袍的报复。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生在中国最时髦的都市,还有个时髦的母亲做样板,喜欢出风头太正常了,而况还喜欢写写画画。喜欢写东西的女人,不管长成什么样子,也不管脾性多么孤僻内向,骨子里也是好出风头的。张爱玲在《私语》里写道:“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可见张爱玲的“风头”里还有很强的女性独立自主的思想。但是,张爱玲不是那种被外界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主张诱惑的,她的思想更多来自经验的直觉,可以说她的女权意识,是被她的没落贵族的封建家庭直接逼出来的。与其说她爱出风头,莫如说好强的个性使然。
布罗茨基曾说,文学的功绩在于确立人的个性。我总是不大相信生活里一个跟风随大流的人,能写出个性强烈的文学。而我相信,人这种社会化的动物,只有文学艺术才能使之成为一个个体。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便是在他们的创作中保持个体的独立性,读者观众则是在阅读、观赏或聆听中,暂且享受片刻的个体存在。张爱玲是少有的在她的文字和生活里都保持了强烈个性的作家。
对于离开上海,我一直相信张爱玲的内心是极不情愿的。她在《诗与胡说》一文里写到她姑姑称赞加拿大如何天蓝草碧,如可选择,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而张爱玲觉得自己断然不可能像姑姑那样爱上异乡,她说:“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就想回家了。”说到这里,读者肯定会想到她晚年客死异乡的孤独。而那孤独也是她主动的选择。八九十年代,海峡两岸均掀起“张爱玲热”,她想回国的话,至少上海是很可能出现欢迎她的盛况的。八十年代初,北大学者乐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曾辗转托人邀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但张爱玲谢绝了。按照世俗的眼光,在当时大陆“张爱玲热”期间不回来,实在缺乏识时务者的聪明,而在精神与人格的层面,她的不识时务令她完成了作为张爱玲的张爱玲,也成为她文字之外的文学延展,与她的作品互补,浑然构成张爱玲独特的文学版图。
她回乐黛云的信里说:“我的情形跟一般不同些,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不想回去看看。”她曾那么舍不得中国,如何在晚年那么决绝地不要回来,哪怕是回来看一眼?这自然和她五十年代出走香港时的经历有关,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她的那段出走俨然已酿成一种“心理创伤”。多年后这“创伤”早已结了痂,但不能触碰,一碰,那痂就可能破了,血又会流出来。
舍不得离开中国的张爱玲,终究没再回家。她把阳台和旗袍留在上海,留给后世的读者想象。
与我内心的起伏迥异的是,常德公寓门前极为平淡,甚至有点寂寥,我特意留心了来来往往的行人,并没有谁去特别多看它一眼,全然不是想象中所谓网红打卡地的热闹。先前网上曝出的大门照片,上面有贴着白色打印纸的赫然黑字“私人住宅,谢绝参观”,那天门上已无那张“安民告示”。大楼正门一旁下方的铭牌上只是“优秀历史建筑”,并无一字提及张爱玲。记得二○○五年挂“张爱玲故居”铭牌时曾专门有报道,另有余秋雨题写的铭牌介绍常德公寓,讲的就是此公寓何以闻名。现在,那些牌子都不见了。
常德公寓,位于上海常德路195号,原名爱丁顿公寓(Eddington House),建于一九三六年的一座高八层的装饰艺术派风格公寓,在如今繁华的现代大厦林立的静安寺商业区,好似一个不问世事的独居老克勒,若不是因了张爱玲,并不会有多少人问津。倘论建筑艺术和历史,上海滩可圈可点的建筑不胜枚举,同是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更著名的则是和平饭店。常德公寓之所以出名,无非是张爱玲先后两次入住。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和她姑姑一起住在51单元,一九四二年她再次搬进公寓,改住65单元。她住在这里六年的光景,是她创作的黄金时期,当年一夜风靡上海滩、近一个世纪后依然令无数读者流连其间的《传奇》和《流言》,就是从这里走向世人的。她在这所公寓里完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比如《沉香屑·第一香炉》《红玫瑰与白玫瑰》《封锁》《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而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孽缘也是从这个公寓开始的,从胡在六楼门缝下塞进的那张求见的字条展开……
从大门上的“安民告示”不再,想来已经鲜有企图拍门入内参观的张迷了,张迷们血脉贲张的热情只能恣意在网上。曾看到有人在网上留言说看到“常德公寓”四个字,就难掩激动,一些张迷更声称将此地当作旅行朝圣地,还有的死忠粉曾因被拦在常德公寓门口不得入内而嚎啕。我喜欢张爱玲,但不至入迷。聪明如张爱玲,在二十出头就看透了世间人情、男女之爱,并冷酷地揭开那携手同行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已是千疮百孔,却仍是要搀扶着前行。可叹的是,她自己却并不因笔下的看透而超然,仍然做了现实里的“戆大”。
我是比不得张迷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死忠。我喜欢张爱玲,准确地说,是喜欢她、钦佩她笔下那么多卓然不俗的语句透出对人情世故的洞见,那些精彩的令人会心的比喻比比皆是,那是文学天才的语言。一个不会比喻,或只会袭用现成比喻的人,写出来的文字大抵是无趣的。她不,她的比喻总是独出心裁,却又符合事物本相,毫无拾人牙慧的滥调。那些被引用得烂熟的诸如袍子虱子之类的,我就不重复了,仅拣出《第一炉香》里面描写葛薇龙姑妈香港山上的白房子在春天傍晚那一段里的一句:“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溶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的灯光,绿幽幽的,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这里的喻依“薄荷酒里的冰块”,和喻体“绿玻璃窗里晃动的灯光”之间的关联,妙不可言,真切可见。还是这篇小说里,她写佣人陈妈和主人家的丫鬟打着一样的辫子,但是,“她那根辫子却扎得杀气腾腾,像武侠小说里的九节钢鞭。”这九节钢鞭的比喻,瞬间将人物个性特征描绘得触目惊心。张爱玲的比喻皆来自生活里细微独到的观察,其喻依,尽是现实世界里的具象的存在,只是被她从生活中搬到纸面上。她说过自己“又那样拘泥,没亲眼看见的,写到就心虚……”(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张爱玲致邝文美信)。
当然,张爱玲比不得鲁迅那样,一提其名,跟着,阿Q、孔乙己、祥林嫂、九斤老太、闰土……就排着队来了。鲁迅笔下的那些人物一直活在今天的现实里,即便不事文学的普罗大众,说到那些人物,也会如数家珍。若论文学人物的典型性,中国新文学史上,无人出其右,而且活生生在那么短小的篇幅里立起来。张爱玲了不得的本事也是善于在不长的篇幅里真切揭示人物的命运。然而,张迷们对其小说人物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张爱玲本人的迷恋,她本人似乎压倒了一切她笔下的角色,她的身世、她的居所、她的衣着、她的发式、她喜欢的食物等等,不一而足。可这些对作家的疯狂追捧,却是在张爱玲本人远在大洋彼岸索居避世时发生的,不知这是市民文化的胜利,还是中国人在当下城市生活里某些缺憾的心理补偿,抑或是对于现实的某种柔软的抵抗?
在美国的朋友看到我在微信里贴出的常德公寓门口的留影,就发了些他的朋友拍摄的公寓内景,张爱玲曾住过的起居室,还有通到她和姑妈家的六楼的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