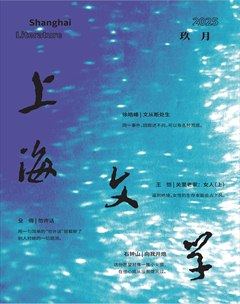一
去年最有意思的收获之一,是重读了《十日谈》。
《十日谈》究竟是怎样一本书?我们可以在各种文学史上轻易找到关于这本巨著的定评。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巨著,是塑造欧洲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传统的开创性文本。换句话说,尽管体裁各不相同,但《十日谈》常常是被拿来和《荷马史诗》《神曲》《一千零一夜》《坎特伯雷故事集》以及《堂·吉诃德》相提并论的古典名著,它们都属于对如今的世界文学版图产生过无可替代的重大影响的源头作品——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一部文学史能绕开这些源头,来谈论文学何以成其为文学。
不过,与此同时,对《十日谈》这部书的解读与阐释也是相当艰巨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部名著的文字有多么晦涩艰深——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看到的中译本都是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小说里的故事也通俗易懂,比起其他“源头作品”来,《十日谈》算是可读性非常强的。但是,《十日谈》的“难”,表现在别的层面:一方面,因为写作年代与当下相隔久远,现代读者往往不易代入古典时空产生共情,甚至对于小说在嬉笑怒骂中表达的“三观”深感疑惑;另一方面,这部巨著的框架很特殊,大故事里套着一百个小故事,梳理这些故事的价值和叙事特点常常会陷入散乱芜杂的局面,不容易抓住重点。因此我们今天的解读,也要从这两个难点入手。首先,让我们来想象一个与现实迥然不同的时空,回到十四世纪的欧洲,来看看诞生这部巨著的时代大致是什么样子。
《十日谈》的写作年代大约在一三四九到一三五三年间。这段时间在历史坐标系上的位置,属于中世纪的晚期,具备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长话短说,这个年代的欧洲在政治上实行封建统治,经济上以封建制庄园的自然经济为主,天主教的控制力达到了空前的强度,其影响渗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态,当然也留下了许多关于宗教裁判所的恐怖传说。相对于现代,中世纪的科技生产水平发展平稳而缓慢,黑死病频繁席卷全球,根据估算前后吞噬了欧洲两千多万人口。人们之所以给中世纪贴上“黑暗时期”的标签,往往与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有关。不过,中世纪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它阴郁、肃穆、僵硬的表面下埋藏着多元化的可能,也孕育着现代社会的萌芽。无论是商业社会的兴起,主权国家和现代政治的雏形,还是宗教改革的发轫,乃至人们在瘟疫阴影中艰难发展的公共卫生系统,都是在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中晚期逐渐形成的。在这段时间里,文化上的突破甚至更为鲜明,高等教育在中世纪悄然成形,伟大的文艺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也都在十四世纪揭开了帷幕。《十日谈》正是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性作品。
以上谈到的时代特征在《十日谈》里不仅都有清晰的痕迹,甚至常常体现在故事的核心价值和文本意图中。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时代因素,《十日谈》就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甚至根本不会诞生。比如说,中世纪天主教控制下的欧洲生活,当时正在兴起的商业阶层与教权统治的矛盾,人性与所谓“神性”的冲突,时刻被黑死病威胁的无常人生,以及文艺复兴初期生机勃勃却又蕴含着认知矛盾的创作环境,都是理解这部巨著的关键词。
当然,哪怕是像《十日谈》这样时代性烙印鲜明的作品,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样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必须在合适的时间遇上合适的作者,才可能产生合适的文本。如果我们稍稍梳理一下创作这部小说的卜伽丘的人生轨迹,就能发现,他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有其独特的经历与背景。
关于乔凡尼·卜伽丘的生平细节,还存在不少争议。公认度比较高的说法是,卜伽丘生于一三一三年,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商人。卜伽丘很可能是他的私生子,童年时代在佛罗伦萨度过,直到父亲被派驻那不勒斯。老卜伽丘对小卜伽丘的设定是继承自己的衣钵,从那不勒斯银行的学徒开始走上商业道路,但小卜伽丘坚决不从,最后他走了一条折中道路,到那不勒斯大学学了六年的教会法典。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法学仍然无法唤起卜伽丘真正的热情。在求学期间,卜伽丘的收获大多来自别的方面:他与国王的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暗通款曲,后者成了后来卜伽丘很多诗文的灵感源泉;此外,卜伽丘在那段时间里出入宫廷、学府和商界。像当时那位比较开明的那不勒斯国王一样,卜伽丘一生广泛结交,无论是贵族、商人还是神学家、天文航海学家、诗人和文学家,都在他的朋友圈里。在他们的影响下,卜伽丘博览群书,创作力旺盛,写了大量长诗和散文体的长篇传奇。这些早期作品尽管大多取材于古典神话,但文本中充满现实感和对世俗生活的饱满热情。我们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能捕捉到作者对于禁欲主义的质疑与讽刺,也能看得出作者在叙事技术上的成熟度。我们甚至能从他写在一三四一年的传奇故事《亚梅托的女神们》里看到多人轮流讲故事的结构。种种迹象表明,《十日谈》的创作思路在卜伽丘的早期写作中依稀可见。
不过,与卜伽丘的创作道路同时进行的,还有他本人及家庭并不平坦的人生际遇。父亲在那不勒斯的破产迫使卜伽丘只能跟随他一起回到佛罗伦萨。在此后的时间里,动荡的政局、不稳定的经济乃至晚年多病的身体,都给卜伽丘的创作生涯投下过重重阴影。不过也有对他的写作和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发生——比如他在一三五○年与意大利诗人、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弗兰齐斯科·彼得拉克的历史性会面。彼得拉克比卜伽丘年长将近十岁,其深厚的古典造诣和“复兴古典”的主张令当时的卜伽丘深为折服,将其奉为终身导师。但丁、彼得拉克和卜伽丘被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巨头,因此,其中这两位巨头的交会与碰撞,无论是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卜伽丘的个人创作生涯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不过,回过头来看,彼得拉克与卜伽丘的性格和观念其实也存在不小的分歧——甚至有研究表明,卜伽丘晚年对于自己的作品的动摇和反思,以及他后来退回保守阵营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彼得拉克的影响。不过,据说也正是彼得拉克,在卜伽丘产生严重自我怀疑,甚至想将《十日谈》付之一炬的时候及时阻止了他,使得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十日谈》文本的全貌。
二
时代风云与个体经历的齿轮在一三四九年终于转到了一个互相咬合的位置:卜伽丘开始创作《十日谈》,写了五年才完工。《十日谈》译成中文后将近五十万字,篇幅很长,但卜伽丘打造了一个精巧的结构,把一百个故事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小说的开篇,他就用一个脍炙人口的引子将这种结构呈现在读者面前。
叙述者在引子里把时间设置在一三四八年,也就是卜伽丘开始创作的前一年,地点在佛罗伦萨,故事的缘起就是在那一年里真实发生的大瘟疫。卜伽丘以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幅仿佛世界末日般惨绝人寰的景象:城里哀鸿遍野,十室九空,从三月到七月就死了超过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