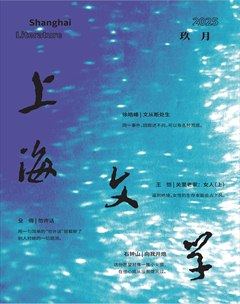如今,小说文本的国际元素越来越常见,“国际”二字承载的世界文化容量,早已不限于域外的建筑或风景。
海外华文写作较易接通国际经络、作者身份与他国情境,赋予“国际化”持续发展动能。“他国故事”也存在国际元素堆叠的事实,借力于实施地方独特性的打造,文本会无形中伏笔着他国与来者之间的隔离带。与“他国故事”相比,“在地写作”的概念弹性更大,它带动国际定制款的华文作品量消减,而趋向以作者本人视野为中心的、以自由和探索为目的的态度与表达。人的主体性被一再强调,地方服务于人,迎合他人、族裔、他国主流的行动被验证为无效,世界华文文学正日益逐步淡化“他国故事”/“中国故事”的题材分区,从而接纳一个整体性的国际。
从破碎的情感到难解的人心
对于海外华文写作,或者说华语旅外写作而言,落叶归根/落地生根两阶段孵化的愁绪,非孤独寂寞彷徨可一并概述。“出国价值”这一关键问题的讨论,一度在“新移民文学”中被成功学遮蔽,华人生存史抹上了自我实现的糖衣。二十一世纪以来,当创作者转向对学成业就者的跟踪调研,他们察觉到新移民中产群体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闷、难以摆脱的烦,即张惠雯小说揭示的“现代病”。张惠雯在“留学生文学”代表作《昨日之怒》里,以“八爪鱼”意象,形容华人对洛杉矶的初印象。八爪鱼有八条触腕,每条触腕又有三百多吸盘的特性,隐喻着无处不在的压迫感和危机感。这一意象很经典,意指盘踞于心的个人欲望,由此情感分析成为解读移民群体心理隐疾的方法论。
情感本可向多维度拓展,华文写作者对情感困境的刻画显然大于对情感富足的描写。对比二十世纪的“留学生文学”,当前小说有着更强的问题意识,能够从现象的陈述延展至绝境的涉渡。写作保持个体—群体—个体的循环思考,主题从被宰制的人生转向被取舍的人心,希望—失望的互搏与互渗培育了作品的核心戏剧性,因其参与庞杂情绪的生成、合成或变异。
唐颖《淑女》(《收获》二〇二四年第五期)中一处亮眼细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上海“出国潮”,妖头、姚哥、小头、黎朶与签证死磕过程中的情感抉择具有时代密度,小说打开下海、出国、回流三个叙事空间,折起黎朶的十年海外生活,秘而不宣的域外婚姻暗戳戳给当事人的私欲下蛊。叶春《定锚婴儿》(《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七期)以话题探讨信任度的底线。待产母亲既然选择在他国生子,就必须生吞与之伴生的所有不适。她没有丈夫、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本能地戒备外界对她的细微窥探,哪怕是一份善意。分娩那刻,女人坚持紧闭房门,拒绝男人的帮助,她认定,终会追随其远航的只有她刚诞下的婴孩。男人发出诘问:“两个完全陌生的男女交换一下真相,不是很好吗?”显然,他低估了信任壁垒的坚硬程度。新生命令两人共同亲历一场阵痛与新生,他们能谅解亲人却无法对世界放下戒心。
从这个角度看,张惠雯的作品对人的情绪表现出极强的共情力。小说既揭示现象,又推衍现象的多种成因,更为原因求取解释。《遭遇》(《上海文学》二〇二五年第五期)讲述一个女人以一封信自揭心灵黑洞。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女人向作家R倾诉其暗恋;刘以鬯《失去的爱情》里,裘旦向“我”宣誓其忠诚;而这里的信是女人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讲述沉积心底的私密事件,小说的新意体现在不为主人公配备倾听者、继而为接下来的信叙事解决合理性,而是确认女性需要让自己成为一名表达者。信理顺了时间脉络,并辅助女性在精神松弛中获得重生。“异物”与“猫”两段经历刻画普通女性的“被侮辱”和“被损害”,噩梦因心理医生刊发的文章重现,她猛然意识到不该由自己背负耻感。我们不会转移阅读注意力在女人的族裔身份上,而是径直奔赴女性的共同遭遇与相似抉择,即“我自己淡化了它们带给我的伤害”,可伤害并不会消失无痕。《遭遇》叙述难言之痛涌动、漾起、平息的起伏,该进程里耸动起的复杂处境,牵动了人性、性别、道德、社会正义等一系列反思议题的降临。
内地青年作家三三赋予常规的澳门书写以新意。《雕像一般的眼睛》(《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十期)设定不同于“叠码仔”故事的新角度,从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记录澳门的“阳光、海风、永无止息的白日梦”。四十年后,罗志伟的返乡之旅,既延续冒险与澳门的关系,又拓宽传统与澳门的关系。澳门岁月原是他认定可自己支配的自我时间,归来后,他惊觉“澳门变成了一座最熟悉不过的迷宫”,惶惑“原来故乡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之中”。渔村在儿媳眼中无比滑稽,在孙辈眼中满是猎奇,老人终究要迎接记忆的彻底爆破。同为内地作家的艾玛,还是以逆向叙事架构《平静的海》(《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二期)。无论在都柏林还是故乡,儿子的日常都是一片静好。父爱缺位和空间距离早已联手制造亲情的疏离,在家/离家两种状态里,游动着“白而轻盈的海雾”。母亲深觉儿子精致的摆拍生活如幻梦,却不敢声张,恐惧失去,她宁愿梦一场。成为失踪案嫌疑人的儿子、出海看鲸鱼的儿子,都令她胆战心惊,深知其心有猛虎,忧心“猛虎下山”。都柏林培养孩子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一个悄无声息的人,又为他摆下一道道前行的路障。小说结尾意味深长,儿子出海就为了看一眼背上插渔叉的鲸鱼,母亲恍然意识到鲸鱼和孩子此刻重叠于一体。
春马《东京都候鸟》(《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七期)里在家乡照顾父亲的长谷川向往东京,朋友高崎和心上人更子先后去东京的选择让他心动,他需破解东京诱惑,踟蹰多年后决意启动一段东京之旅。居酒屋和出租屋的晨昏,将一切为生存搏命的男女送至他眼前,长谷川在醉与醒之间试图捕捉一些东京的轮廓,可东京不会给他短暂思考的机会。安心当一只候鸟,才是缓解心灵疲惫的合适方法,他知道“该回家了”,短短两天就与东京不辞而别。小说的研究对象是当下日本青年人群体,它提供一个由日本御宅文化培植的视点,即维持现状反而最好。姜若光笔下《一个二十五岁女孩的一生》(《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七期)是发生在圣彼得堡的哲思。“我”和孔雀初次见面就约喝酒,对谈围绕一个因“我”而死的女孩,正是这一面之缘改变了“我”的命数,即从数学博士后到潜水衣生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