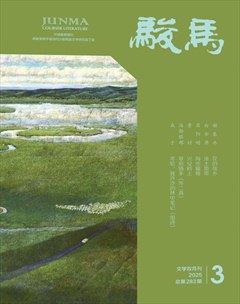八卡
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写在书本上,比如草甸子是花的故乡这件事,只有额尔古纳人心知肚明。
花躲在草的怀抱里,等到太阳一声令下,所有的花都跑出来了。草甸子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花,好像一群喜气洋洋的人换上鲜亮的衣裳正准备欢度佳节。花在它们的故乡比在花农的花圃里或者城市的花坛里恣意多了,它们可以生长在任何地方,河套里、山坡上、滩涂中、碎石堆里、马路旁,也可以单独或者几种、十几种、几十种花挨着花地挤在一起。
不同的花拥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单独生长的花集中连片浩浩荡荡,如同花的国家,比如八卡的芍药和三队草甸子上的黄花菜;不同种类的几种、几十种花蜂拥着挤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多民族团结的花的国家。
土地是黑色的却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来,土地想表达什么?如果没有公路、城市以及村庄拦着,这些花会不会爬满所有的山岗和草甸子?如果不被人的眼睛看见,这些花是不是白开了?
花的故乡除了花还有什么?大约半个多月前,我在黑山头到室韦的边境线上走了一趟。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路过这里,公路两旁的黄花菜与野罂粟正开得如火如荼。我中学的生物老师说自然界最普遍、存在最多的花是白色的花,但那时放眼望去则满眼都是黄花。他说开花是草场退化的一种表现,这让我的少年时代充满了忧虑,因为我看到的草甸子都开满了鲜花,难道我家的草场退化了?他还说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饮料是人尿,幸亏这个可怕的预言没有实现。
过了黑山头古城,移动手机提示正在接收俄罗斯的基站信号。两年前,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正在采黄花菜的边民,他并不是传统华俄后裔卡民的后代,他受雇于七卡山里的某个牧业点,已经来此十多年了。他像个主人似的接待了我们并邀请我们同他一起采黄花菜,他说快采点儿吧,这是今年最后一茬了,再不采就没了。他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问我海拉尔到室韦新修的公路通车了没有?其实已经通车好几年了。他说再过几个月大雪封路后他就不下山了,村口的小卖部会把他需要的物资从外面带回来。
野罂粟迎风招展,黄花菜却还隐忍未发。一只狍子出其不意地从河套蹿了出来,这只鹿科动物头顶漂亮的花犄角在额尔古纳河畔开满鲜花的草地上跳跃着与我的车并辔而行。我想它要是这样一直陪我跑到八卡就好了,但它跑了一半就后悔了,开始掉头往回跑,也许是想跑回去迎接下一拨客人。
八卡是边境线上一座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屯子。在进入八卡的村口时,几名彪形大汉席地而坐,其中一名壮汉问我从哪里来干什么去?我说从拉布大林来,到前面去……我的话还没说完,这名壮汉脸上的表情突然莫名其妙生动起来,他截住我的话头接过去说,是去看……说着用手向前一指,我说是的。
是什么让一个中年男人的面孔变得妩媚并让两个陌生人心照不宣?是八卡的芍药。这两年八卡的芍药火了,有些人和地方为了出名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八卡却因为芍药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各大自媒体,人们纷纷从大老远的地方跑到八卡来看芍药花。当然草甸子也是芍药花的故乡,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将长满芍药的野甸子与土豆地相混淆,两者之间最大的相似性在于它们共同拥有白色与淡粉色的花朵以及面积的广阔。
到达芍药坡,发现很多人已经捷足先登,山坡上挤满了花朵与赏花的人。八卡的芍药火了以后,别的乡镇也陆续推出自己的芍药坡,但名气与规模都不如八卡。芍药这十几年被盗挖得太厉害了,现在它们开始用美丽来拯救自己,我看到八卡的芍药已经被用木板障子围起来了,以示保护和重视。
端午节去三队草甸子采黄花菜时,我父亲说,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二斌的牧业点儿上,我父亲说二斌从海拉尔铁路辞职后,来这个出牧点儿养羊,二斌的羊养得好,不但身为老板还兼职羊倌。二斌在他放牧几千只羊的那面山坡上长年坚持和盗挖野生芍药的盗贼做斗争,从而保住了那一面山坡的芍药,就是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甘大垓那面芍药坡。
我们采黄花菜的时候,头顶花犄角的狍子又跳了出来,除了狍子我还遇到了一只赤麻鸭。当时云雀与百灵鸟在我头顶看不见的地方开锅了一样叽叽喳喳,一只赤麻鸭就在离我不到十米远的地方气定神闲地站着,清早的阳光打在它身上散发着耀眼的金属质感的金铜色的光芒,好像传说中的神鸟凤凰。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观察这种大鸟,十几年前我同林业局防火站的同事在额尔古纳湿地自然保护区踏查时,一只赤麻鸭突然嘎嘎大叫着从我脚底下的草窠子里冲了出来,把我吓了一跳,等我回过神来,它已经慌里慌张逃上了天。那几天我在湿地的草甸子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鸟,成双结对的灰鹤与蓑羽鹤、成群的乌鸡与凤头麦鸡、金雕与鸱鸮盘踞在最高的树杈上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仿佛这是魔法世界的入口。那时候春天的雪刚刚融化,青草还没有长出,这些鸟守候着灰褐色的光秃秃的大地静待花开,等着大地绿起来。
端午节的第二天我们去海江哥家的出牧点儿上采金莲花,这次等在花海里迎接我们的除了蹦蹦跳跳的狍子还有拖着长尾巴的环颈稚,这些美丽的花朵如果只被人类的眼睛看见会显得多么的寂寞;如果不被人类的语言赞美又会显得多么的遗憾。
月亮谷
这是一个弧形的山谷,海江家的牧业点儿驻守在谷口,门前一条弯曲的道路绕过一座小山,勾画出一个新月形的山谷。山谷的尽头是另外一家牧户的牧业点儿,陡峭的山崖上层层叠叠的白桦将这片山谷的三分之一包围起来,另外的三分之二交给了上库力农场的麦田与油菜田,排列整齐的麦田与油菜田浩浩荡荡,以防止这个山谷里的花朵跑到别处去。
这片山谷地势起伏,去往海江家牧业点儿的路上依次呈现如下风景:初春的新绿在山岗上蔓延开来的时候,牧业点儿淹没在一片蒲公英鹅黄色的花海中。二十几天后,黄色的花朵变成纤巧的毛球,庞大密集的伞球犹如云朵般覆盖着整片山岗,海江家的牧业点儿不起眼的小房子像欧洲中世纪的古堡一样一点一点在一片梦幻般的云朵中隐现并缓缓抬升。远处的山岗与农田弥漫着淡蓝色的雾霭,随后银莲花、野罂粟、黄花菜、金莲花、八月菊陆续登场。
所有的花朵都在这片山谷找到了归宿。与人为种植的花朵不同,这片山谷里的花朵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存空间。大片大片的金莲花与黄花菜繁华着谷底湿润的平地,这些莲花状与喇叭状的花朵盛满山谷金色的阳光、不染纤尘的星光雨露与空气、清爽的风、云雀与百灵鸟的啾鸣。金莲花清热解毒,黄花菜除了美味还是治疗这个世界较难治愈的一种疾病——忧郁症的良药,这些携带天地间最纯正能量的花朵年复一年的缤纷在草原深处并治愈着人们的生活与心灵。白色的瓣蕊唐松草夹杂在黄色、紫色的大花鸢尾中;匍匐在地上的点地梅与裂叶堇菜接住从叶片间漏下的阳光,开出星星点点的白色与紫色的小花;火红的萨日朗统治着向阳的坡地,萨日朗分两种:细叶百合,植株矮小花朵鲜红。斑点百合也叫大山丹,植株可达2米,橘红的花朵上带有褐色斑点。这些通红的花朵漫山遍野,好像大山丹在山上喊了一嗓子,所有的百合都跑了出来,紫色的并头黄芩与红色的火柴花慌里慌张裹挟其中;蓝色的勿忘我与粉色的打碗碗花跟头把式地落在最后;蓝色的翠雀开在长满白桦的山坡上,好像从白色的城堡里走出来的一群穿蓝色裙子的俄罗斯少女;野生芍药盛开在山谷最深处,那些硕大的粉色与白色的娇艳花朵令它们身边的一众花朵黯然失色。此外,一簇簇丛生的高大玫红色的柳兰守候在田间地头,是田野派来的迎宾使者。
一条暗河贯穿了整个山谷,这条由地下泉水喷涌而成的水流滋养了整个山谷。茂密的植被完全遮盖住了泉水,只有在谷底植被最葱茏处,一人多高的牧草掩映下,密集的塔头墩开始令人寸步难行,才能看到清澈的水流蕴藏其中。一路在山谷间曲折跋涉的泉水依山势而下,在山脚下汇集成一处潭水,这是塞外版的《小石潭记》,高大的芦苇、光辅香矛、黑麦草海浪一样簇拥着泉水一路荡漾而来。海江家的牧业点儿坐落在水潭旁。蹚开高大的牧草,紫色的云英、蓝色的矢车菊、白色的麦瓶草迅速向两边躲闪,一眼清冽的潭水冲刷着青翠的水草,像一颗明亮的眼睛般闪烁在草原深处。直径十来米的水潭深浅不一,水流从茂密的牧草间注入,又从水潭的另一端重新隐没于草原,好像这些水是草生产出来的,或者这些草的工作就是护送这些泉水去远方。从地下深处涌出的泉水冰凉沁爽,海江常常用它来冰镇西瓜,或者将新鲜的果蔬肉类装入密封袋中投入水潭,盛夏时节可保一周不腐不坏。
茂盛的水草与丰沛的水源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候鸟,这些鸟混迹在海江家牧业点儿的鸡鸭鹅群中,俨然成了牧业点儿的一部分。一群居住在水潭旁的由十几只鸿雁、一对蓑羽鹤、两对鸳鸯、几只赤麻鸭组成的团队是一群开在天空的花朵。它们栖息在水潭旁的草窠子里,除早晚振翅在开花的山谷间各巡视一番后,其他时间则徜徉在草海中等待海江的投喂。偶尔有闯入山谷的车辆骚扰这些大鸟,海江就冲上去同他们理论,逐渐再没人招惹这些鸟儿。
海江清楚地了解每一只大鸟并为它们起好了名字,这些鸟与海江在从初春到深秋南来北往的一次次迁徙中成了彼此无法割舍的一部分。每年开春,海江两口子都像惦念自己出嫁的女儿或者多年的老朋友般一遍遍念叨这些鸟怎么还不来?或者要什么时候来。有时我去牧业点儿,海江哥与嫂子也同样对我说,鸟来了或者没来。鸟来与不来都是这个山谷与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山谷除了盛产花朵还盛产蘑菇,蘑菇是狍子的口粮,我在山谷采蘑菇时,时常险些与狍子撞个满怀,我和狍子都吓了一跳。有时,我们隔着白桦的枝杈远远地发现了对方,然后扭头各走各的互不打扰。
白天棉花糖一样的云彩一团一团地飘荡在山谷上方,高大的麻花头、大花葱、益母草屹立在山谷以防止云彩掉下来。千军万马的麦田与油菜田从远处跑过来,到达这个山谷时却害羞似的止步不前。夜晚的山谷则变了模样,蓝灰色的夜幕隐去了远山与田野,月亮从山岗上爬上来,被月光灌醉的花朵低垂,狍群从白桦林里跑出来巡视整片山谷,急吼吼的狍群用叫声唤醒即将沉睡的花朵,连同这片土地很久以前的记忆。很久以前,这里的牧草有一人多高,那些同样高大的花朵荡漾在浩瀚的草海上,风一吹,好像大海泛起的七彩浪花。
毛毛狗与耗子花
此前我并不知道毛毛狗是柳树的花朵。通常我见到它们时,它们已被从枝头上折下来,插在水瓶子里,摆在窗台上。直到几年前,我在八连河套采访一位放蜂的老人,他说他家的蜜蜂四月初就要在河套采百花蜜了。四月初的积雪还未化完,哪来的花与蜜?对此,我立刻表达了质疑,老人说采毛毛狗的蜜。那时我才知道这些花生米大小的毛茸茸银灰色、灰白色的毛球竟然是红毛柳的茸芽花蕾。
经历了漫长的隆冬,还有什么比春天更让人期盼的呢?我小时候就经常看到大人们在冰天雪地的河套里捧回一把一把的毛毛狗。与南方的柳树不同,红毛柳需要抵御零下50℃以上的极寒,它们像炸蓬窠一样尽量多抽出枝条并努力将自己举向太阳。
毛毛狗来了,春天就来了。毛毛狗是来给耗子花探路的,毛毛狗来了,耗子花就来了。耗子花也叫白头翁,全株覆盖着白色绒毛。大概我们这个地方太寒冷了,来报春的花朵都自备了一套御寒的厚衣裳。我小时候并不知道还有耗子花。耗子花开在荒僻的野地里,那时候人们刚从严寒的怔忡中回过神来,褚褐色的大地空无一物,耗子花不起眼的矮小身影潜藏在石头堆里,不用心寻找,根本看不到它。
后来,当我有能力踏足荒野,我才看到这种毛莨科植物从枯黄的杂草和碎石堆中脱颖而出,它们舒展着同样毛茸茸的大面积的紫色、红色、耦合色、白色的铃铛形的花朵,迅速拯救了早春单调的视野。柳树跑到南方就变成了烟花三月的垂柳,报春的花朵也一路向南变幻着各种撩人的姿态,这些红毛柳与耗子花寂寞地长在这里,它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几年前,我看到父亲采来早春的耗子花塞进一只玻璃瓶中并注入高度白酒,等到白酒没过花朵封存一段时间后,花与酒的颜色都变成了深褐色,父亲就将它们取出敷在膝盖处用来治疗关节疼痛。
关节不适是我们这个高寒地区的常见疾病,父亲说老人们都知道这个偏方。父亲还说以前缺医少药,遇有感冒发烧,人们将红毛柳折回煮水喝就能消炎祛火,治疗头疼脑热。
红毛柳是护岸柳,它们站在河的两岸尽心守护着草原上的弯弯细流。早春愈发通红的红毛柳像冰雪中燃烧的一团火焰,一粒粒卧满枝头的毛毛狗满天星一样弥漫成一片片蓝灰色的雾霭,等到银色的绒毛间伸出一根根嫩黄色的蕊,那是早春的冰雪中最温柔的一抹亮色。红毛柳守护河套,耗子花则守护旷野。大自然早就安排好了,植物生长的地方,就是人类最美的家园。
星星海
来到这里我就后悔了,车子陷在草窠里寸步难行。盛夏的牧草长势凶猛,这些密密麻麻的草挤在一起,根本没给人留地方通行。我在草丛中艰难跋涉,一人来高的荒草迅速吞没了我,十几米外森林一样的芦苇正荡漾成一片海洋。我好像掉进了一个等待多时的陷阱里,章鱼一样的触手从四面八方伸向我,高大的牧草带着被惊飞的无数蚊子蠓虫在我身边快速躲闪又回弹到我的脸上身上,裸露的皮肤很快就被像轰炸机一样毫不留情的蚊子留下一层火辣辣的大包,加上被杂草牵绊住的脚步趔趄,一阵阵窸窸窣窣的感觉沿着脚踝、裤管不断向上攀爬和漫延,我很快就败下阵来。我一头扎回到车子里,闷热加上被蚊虫叮咬的剧烈瘙痒令人烦躁异常。
这里是上库力六队田地里的一处湿地,芦苇从远处看好像一片绿油油的草原。芦苇中央一眼泉水汇集成的湖水滋养着整个湿地也吸引着无数鸟儿聚集于此。我静静地坐在车里,等待着蓑羽鹤与赤麻鸭在我面前翩然起舞。然而并没有,高大的牧草像堵墙一样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除了蚊子蠓虫的“嗡嗡”声与它们“砰砰”撞击车窗玻璃的声音什么也没有。
但我想既然已经来了,不如就此等等看,说不定那些鸟儿此刻正潜伏在某个角落窥视我。天色一寸一寸地暗下来,我将汽车的后座放倒躺进车里,天彻底黑透后,四周陷入了海底一样的黑暗与死寂。我在这片湿地见过狍子、鸿雁、苍鹭、野鸭等。遇见狍子时,我正举着望远镜向远处瞭望,根本没注意到对面钻出来的三只狍子,狍子也没看到我,狍子与我几乎撞在一起。那时上库力农场的大型农用机械正轰鸣着在旁边的田地进行秋收作业,而此刻,盛夏的作物已进入稳定的生长期,根本无需抚育与田间管理,田野里空无一人。
这是个奇妙的时刻,我深陷在荒草的中央,躺在草丛中看着星斗一点一点地从草尖上爬上来。草叶抖动如脉搏颤动,荒野万籁俱寂,星光折射在牧草上的阴影勾勒出宇宙无涯的距离,亿万斯年的时光在草尖上轻轻抖落成生命的蓬勃律动。我入定般地躺在车里,好像我正变成岁岁轮回的一株野草,日月洪荒在我身边倏然滑过。
北斗星如弯弓,正对着右侧的车窗。上一个年轮的深秋,我在这片田野见到过一串星链。那时大概是夜里9点半左右,满天的星斗在没有任何光污染的湛蓝夜空中散发出类似钻石一样的灼烁光华。我正站在洒满秋霜的裸露着麦茬儿的黑土地上向星空眺望,一串星链像一列火车一样悄无声息地从我头顶上驶过,我猛然发现它时,几乎惊慌乱到失语。一串明亮的由十几颗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卫星滑过树梢,滑过我的头顶,带着一种无声的节奏向远方而去。它们的光亮似乎由星体的两侧射出,深蓝的夜空下,好像《千与千寻》中驶入海底的火车,或者一列透明的火车长出翅膀缓缓向天空飞去。
我注视着夜空,昏昏欲睡。我没有再次见到星链,车窗外北斗星勺柄处“开阳”与“瑶光”两星间一侧漆黑的夜幕中陡然惊现一枚亮点,亮点光芒在几秒钟内急剧扩张,亮度与体积俨然超过一等星。我在惊讶中不可置信地从车中坐起。传说北斗星原有九颗,除现有的七颗外,“开阳”与“瑶光”两星间左右各一侧另有“洞明”与“隐元”两颗隐星,先秦文献亦记载“北斗九星,七见二隐”。紧接着,陡然出现的炽烈星光又在几秒钟内迅速塌陷直至虚无。大约间隔一秒后,星光再次迸现并越来越亮,快速扩张的超强光芒甚至掩盖住了周围的星辰,我已经做好了迎接一场宇宙大爆炸的准备。然而,如同它的出现,这些光芒再次快速在夜空中敛尽。
好像来自宇宙深处的两声尖叫,不知这些星星在忙些什么。这遥远的星光是否来自一场恒星塌陷与超新星爆炸?我在一片漆黑中胡思乱想着迷迷糊糊睡去,我梦见一颗星星像太阳一样悬挂在我的头顶,夜晚明亮如白昼,狐狸与野鸡站在草窠里傻乎乎地与我对视……夜晚的车内潮湿而阴冷,我翻来覆去地醒来又睡着。不知过了多久,好像我的等待得到了回应,“啊”的一声鸟叫彻底将我从梦中拽醒。
巨大的寂静托起这鸟叫,好像它是这片土地的守夜者。鸟儿的叫声嘶哑平静且从容,在空旷的田野传来回声。但“啊”是个感叹词,不知这只守夜的鸟想汇报什么。我从黑暗中坐起来,更深的夜像墨汁涂抹车窗外。我将后备箱打开,青草的香气与裹挟着星光的夜色扑面而来,流通的空气使车外比车内显得干爽。我用力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下车伸展了一下腿脚,鸟又叫了一声。午夜的露水已令蚊虫无法高飞,我小心翼翼地拨开身边的杂草向前走去,脚步踩在草丛上的“唰唰”声显得格外清晰而巨大。远处的鸟儿陷入了沉默,跨过身边的杂草一路向前走去并向天空望去,盛夏的银河如同一幅巨型蛛网悬在头顶,密密麻麻的星辰组成的海洋由南向北贯穿了整个田野。那些不同亮度、密度、大小的星团纵横交织在一起,如同梦,仿佛来自宇宙的一声声惊叹。我仰着头,感受着这些梦幻的光海一点点的下降并降临到我身上。
这时鸟又叫了一声,我一低头,发现同样密密麻麻的油菜花海已将我包围。那些油菜花从与银河相交的远处跑过来,每一朵花都对应一颗星星,它们把嘴巴张成一个个圆圆的“O”型,无数朵花共同张开嘴巴呼喊,那些巨大的声浪被遥远的星光听见,星光与花海互相交叠。这是一曲来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室女座星系团——银河系的交响乐,类似于《黄河大合唱》,忙碌的卫星也参与其中。我在田野里听见,播种的人在梦里听见,你在哪里听见?
【作者简介】谢春卉,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作品散见于《骏马》《美文》《草原》《青春》《光明日报》《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曾获全国首届“美丽中国”征文一等奖、首届“林非散文奖”、呼伦贝尔市文学艺术创作“骏马奖”、《草原》文学奖等。
责任编辑 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