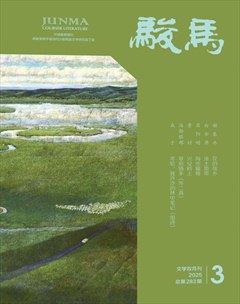二十年前的一个夏天,跟着一朵流云,我一路北上到了呼伦贝尔,远嫁的堂姐在那里安家落户。
坐上横穿内蒙古的草原列车,穿越了沙漠和荒原,一路向北,我才知道呼伦贝尔的绿是有重量的。在我的潜意识里,静卧于内蒙古北部边陲的呼伦贝尔是苦寒之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为堂姐担忧,我们一起长大,她自小娇生惯养、衣食无忧,能习惯另一个地方的生活吗?可是当列车碾过北方的荒凉,进入大兴安岭的余脉后,车窗像是突然被夏天撞开似的,铺天盖地的绿一下子涌了进来。
透过车窗,几百公里的绿连绵不绝,翠绿的草地与湛蓝的天空相互交融,在天地相接之处,成群的牛羊如繁星般散落其间。“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幅壮丽景致生动鲜活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其实,这里并不荒芜,早在史前时期,便有人类在呼伦湖畔繁衍生息,开启了与它的不解之缘。
下了草原列车,途经海拉尔,我又坐上了开往根河市的大巴,再向北。堂姐家在根河市伊克萨玛林场。通往林场,有一条蜿蜒两百多公里的林区公路。在这条公路上行驶,疲惫的身心瞬间就被浓郁的绿色紧紧包裹,四周静谧得让人敬畏,心也随之安静下来。这种深绿,给人绿野仙踪般的梦幻与神秘。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终于抵达了伊克萨玛林场。堂姐家的木刻楞房子古色古香,像块浸了蜜的方糖,嵌在草甸子上。木屋向西不远处,有一片原始山林。寂静的山林,大片的草地,摇曳生姿的花草树木,悄无声息的湖泊树影,蜿蜒曲折的林中栈道,还有一辆辆停歇下来运木材的小火车……看着眼前的一切,除了惊讶,我更多的是欣喜——原来呼伦贝尔骨子里隐藏着这样的浪漫与惬意。
我和堂姐三年未见。一见面,堂姐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堂姐胖了一些,圆圆的脸被林场的风吹得红彤彤的,身体更加结实了。
“怎么样,一路上累了吧?不过,很快你就会喜欢上这里的,因为呼伦贝尔的绿会咬人呢。”堂姐开玩笑似的说。她把新挤的冒着热气的牛奶端上桌,又抓了一把炒米和奶皮子丢进碗里时,我瞥见她粗大又发红的手指节。眼前的堂姐是熟悉的,她和小时候一样爱说爱笑,梳着两个麻花辫,保留着小女孩似的天真;眼前的堂姐又是陌生的,她娴熟地煮着奶茶,切着手扒肉,很自然地就拿起了套马杆,吆喝着牛羊,好像她这个外乡人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久,是呼伦贝尔的一部分。
她切下一条子羊肉放进我的碗里,说自己散养的羊吃着青草,喝着山泉水,听着自己唱的小调长大,味道鲜美得很呢。她又说刚来到这里放牧时,房子外面的草能长到没过马肚子,夜里风吹过时,整个草原都在簌簌地咀嚼月光。如今围栏圈住了草场,牧草矮了半截,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牙齿啃过似的。
堂姐正说着,堂姐夫走了进来。他身材高大魁梧,颧骨高高的,脸像山上的岩石一样黝黑发亮。堂姐夫也很爱笑,他和堂姐笑起来的眼神一样,动作一样,就连嘴角上扬的弧度也是一样的。堂姐夫是伊克萨玛林场的一名伐木工,鄂温克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
透过堂姐明亮的眼睛,我似乎看到了她东边牧马西边放羊,堂姐夫深山伐木的模样。
吃过晚饭,在堂姐轻柔的絮叨中,我把疲惫像扔一件旧袍子一样丢下,倒头就睡。夜里我听见风吹白桦林“哗啦哗啦”的声音,有一种在深山老林却置身于茫茫大海的错觉。风大了,好像又下雨了,落在木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我在风雨的呼啸声中沉沉入睡。
第二天清晨,推开门,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阳光里碎成千万片翡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