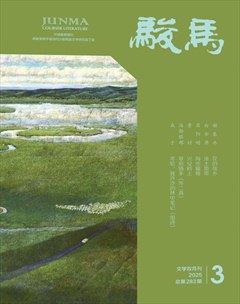我的故乡呼伦贝尔,它的风流不仅在于夏日草原的一碧千里,秋日大兴安岭的层林尽染,呼伦湖、贝尔湖连天的浩渺烟波,还在于它生长着厚重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
多元化地貌所呈现的生态之美富有层次性,这片北疆之地依照时令捧出深情的赐予:芍药、桔梗是花,也是药材;柳蒿、蕨菜是草,也是珍馐。春天成片的黄花吹起欢庆的喇叭,夏秋满山的蘑菇撑起诱惑的伞。诗意的呼伦贝尔,它的一草一木尽得风流。
心若明媚,便可一路芬芳
阳光照亮春天,山林原野,绿草葳蕤的地方经常闪动野菜的身影。野菜依照时序次第登场,最先亮相的是蒲公英,脚跟脚来的是柳蒿,黄花紧随其后,蕨菜踱着方步走来时,已是盛夏。
蒲公英,我们这儿叫它婆婆丁,它可入药,可晒茶,嫩叶可做成菜肴。
蒲公英在野菜世界称得上颜值担当,且性格豪爽。它的花朵饱满,像老天的金币袋子漏了,撒得遍地都是,金灿灿的,闪着诱人的光。蜜蜂来了,黄蝶来了,飞入花丛无处寻觅。
蒲公英简直发了疯,医院墙外、广场前面、楼头街角,只要有草的地方就有它明艳的黄花。
同学发来视频,她和朋友自驾游,抵达一片湿地。那里蒲公英绚烂如霞,花连着花,朵连着朵,一片耀眼的金黄,简直美极了,说一半是草一半是花,毫不夸张。大家雀跃着下车采花,拍照,疯跑,快乐得像孩童,真想追了去,与她们一起在花海踏浪。
蒲公英的花谢落,蓬松的绒球连成一片,恍惚间以为荻花抢戏。蒲公英的孩子乘着风旅行,去远方寻找新天地,写一首自己的小诗。从春到夏,这片金色凋谢,那片金色盛开;这边银色飞离,那边银色登场,以此感谢季节的馈赠。
如果说一朵花是一张笑脸,草地便是一面笑脸墙。傍晚散步时,我被占满草地的蒲公英花牵住,拍特写,收它的恣意在麾下。回到家,我家先生拉我到窗边:“还用去远处拍吗?咱家花园里就有。”我家楼前是一块草地,从窗口看出去,只见绿草青青,不见金色花朵。他吃了一惊,密密匝匝的小黄花被谁收走了?
那一夜,我睡得极不踏实。转天,起早跑去草地察看,一场虚惊——蒲公英花都在,花瓣合拢藏身于草丛。阳光挥动手中的魔法棒,一枝花变成一株草。蒲公英的花瓣居然手掌一样张开,我像法布尔发现蝉有听力一般欢悦。为自己过去的粗心汗颜,号称花痴,对花的习性却所知甚少,妥妥一个叶公。
一直以为花会不眠不休,白天与太阳恋爱,晚上与月亮说悄悄话。自从发现蒲公英的秘密,一有时间我就去草地研究一番,看花仙子里谁是夜猫子,谁喜欢赖床。有的花跟人一样按时起居,日出而开,日落而息,顺应自然法则;有的花喜欢晚睡晚起,不管别人怎么看,活得随心随性。如此,才构成多姿多彩的自然界。
蒲公英梦想着去远方,远方有多远,风说了算。河滩、沟渠、砖缝,即使身不由己,所遇土壤贫瘠也不怪怨,从容扎下根,不畏风雨,一心一意开出花朵回报大地。一朵小花就是一个深情的吻,暖暖的金色的吻。
蒲公英随缘自适,我不觉想起苏轼的词《定风波》中的那个女子。王巩被贬蛮荒之地,歌伎柔奴随行。柔奴“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岭南风土不好,她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身处逆境,如果能安之若素,旷达乐观,像蒲公英,像柔奴,像苏轼,心若明媚,便可一路芬芳。
库木勒的春天
春风轻轻呼唤,憋了一冬的柳蒿破土而出。这时的柳蒿通体红色,如一朵红云漫过女孩的脸颊。羞涩的红渐渐退去,青葱的绿手挽着手连成一片。柳蒿嫩的茎叶可食用,人们习惯称它为柳蒿芽。
三三两两的黑白花奶牛摇着尾巴啃啮着青草,羊群云朵一样在绿色的小丘上移动。在荒滩湿地、河边柳丛,人们拎着桶,挎着筐,弯着腰,手采或刀割柳蒿芽,耳边风的呢喃叠加着采柳蒿的欻欻声,这情景是一幅有色有声的动态画。
柳蒿被割过的地方像剃头后冒出的头发茬,清虚虚的。柳蒿如韭菜一般,割过一茬再长一茬,这是许多草本植物再平凡不过的本能,人类却难以企及。再生能力是一种不屈的倔强,即使遭遇灭顶之灾,仍要重整旗鼓,在哪里受伤,就在哪里萌发新芽,以向上的繁荣疗愈伤痛。根即是柳蒿的心,只要根在,就有机会再次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