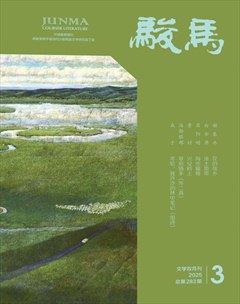那天要是不去医院,癌不了。
爷爷稍闲下来就这么想,大半辈子了,就没登过医院的门。“吃片药就好了!”这是娘一辈子的口头语。小时候感冒了,娘硬给灌袋平热散,捺到炕上,从头到脚捂上大被发汗,憋得喘不过气,也不敢吭声。娘厉害,说一不二。直到娘伸进手摸我头上的汗滑溜了才掀开被,感冒也就好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老伴儿从来不吃药。她不吃,也不许家人吃。“是药三分毒,挺挺就过去了!”这是老伴儿大半辈子的口头语。爷爷也从不体检,年年发的体检表从来不用都白瞎了。他说,人的身体就像一个火车头,年头到了,部件哪能没点毛病,还用医生说!年轻人和老年人都用一把尺子检,能查不出病来?不查出病来,医生靠啥活着?体检科就是造病科。爷爷更反对一查出病就动刀动枪,切这儿割那儿。他说,这就像年轻人拌句嘴就闹离婚,这是过日子?
肚子偏偏不给自己助脸,狠狠打了他一巴掌。
离年不到一个月,大徒弟的二儿子结婚,给他寄来大红邀请函,手机里又再三说,师父,一定来,带着师娘。爷爷说,不让去,我也去!他退休后定居扎兰屯,很少外出,巴不得和徒弟们聚聚。他儿子结婚那年,家住各地的徒弟们都来了。那天,徒弟们都护着他少喝,他还是喝高了,第二天一天没下炕。吃午饭时,儿媳妇儿一个劲儿问,爸哪去了?气得老伴说,俺俩昨晚离了!说着,眼泪就掉下来。还是大徒弟会打圆场:师娘是说气话,师父是铁道部劳模,铁路局长来咱这儿视察工作,点名让师父去作陪。这故事直到现在还是杨家一个保留段子,成了一家老少和谐的重要粘合剂。当然,儿媳早就知道那天老公公是喝高了。这次H城之行,老伴也想去,一是她也特别喜欢大徒弟,二是去看护老伴。可孙子毛毛还没放寒假。孙子像爷爷,也喜欢热闹,一家人去多好!
爷爷到H城的第二天,大徒弟儿子结的婚。那天晚上,新郎新娘都入洞房了,他们师徒几个还在酒桌上喝呀唠呀。徒弟们还是护着师父,劝他,让他少喝。他一杯没少喝,但一点儿也没上头,头脑清清的,嘴叉子还嘎嘎的。真是喜酒不醉人!这喜,当然不光是孩子的婚事,各种喜都在杯里装得满满当当。
第二天爷爷早早起了床,惊醒了身边的大徒弟。昨晚,大徒弟把几个师兄弟都安排在宾馆,又把媳妇儿撵到小屋,他和师父睡在了一张床上,几乎唠到天亮。大徒弟问师父,起这么早干啥?他说,看看松花江去。大徒弟忙起身穿衣要陪他去。他正色道,睡你的吧!我还没痴呆!大徒弟没话了。他顶着寒风,去了江上。爷爷上班时,他们博克图机务段的车跑不到H城。有一年,他的机车需要大修,来到这里。那是夏天,H城真美,特别是松花江,师徒们整整逛了一天。大徒弟说,博克图和H城连着,不光靠滨州线,还有雅鲁河。雅鲁河发源于大兴安岭上博克图的沟里,往南流经扎兰屯,入嫩江,然后汇入松花江。有首歌叫《太阳岛上》,爷爷常用唢呐吹。眼下的松花江没了滔滔江水和朵朵浪花,一片冰天雪地。江面上立着各种各样的冰雕迎接就要到来的春节:龙腾虎跃的,楼台亭阁的,十二生肖的,都活灵活现。爷爷是头一回看到这样好的冰雕。博克图也有冰雕,哪有这里的规模和气势。他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琢磨,大徒弟打电话催他回去吃饭,他一遍遍说马上。
太阳升起来了,他往回走。路上,一辆救护车叫着,停在了一座大楼前。他扭头看了一眼,那是一家医院。肚子不舒服隐隐约约有一年多了,他没和任何人说,他怀疑是上班时,饥一顿饱一顿,冷一口热一口落下的病。没啥大不了的,自己当年是段上万米第一、摔跤冠军。但此刻的他突然想去医院瞧瞧肚子。都说H城医生的医术高,好不容易来一回,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就一分钟工夫,爷爷坚守了大半辈子“挺挺就过去了”的原则失守了。他迈进医院大门时,嘴里还念叨着刚想起的两句歇后语:搂草打兔子——当捎带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他觉得第二句不中听,他一贯反对大人打孩子,把它改了顺口溜:下雨天磕毛磕——闲着也是闲着。
医院刚开诊,他很快排上号,问诊,拍片一切进行得顺顺当当。他坐到大夫面前,大夫问他家人谁来了,他说老伴儿想来来不了。大夫阴着脸看了他片刻,送上了晴天霹雳:结肠癌晚期。真的?大夫。爷爷直眼问大夫。大夫也直眼看他说,我也希望是假的。又补充,需要立即办理住院。爷爷感到天昏地暗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也不回话。片刻,他攥起CT片子踉踉跄跄出了屋,一屁股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双手捂住脸,低下了头,泪水就从指缝里淌了出来。片刻,他骂了自己,妈的,你不总说你不怕死吗!泪水还是从指缝里往外淌。他擦着脸抬起了头,他想通了!铁道线就是日子,火车是时光,人都是旅客,早到站,晚到站,早晚都得到站,到站了都得下车,票就买到这一站。司机也是旅客,也有下车的钟点。火车头全身是铁也有报废的那一天。其实这道理他早就懂,常和师兄弟们这样说。七十多岁了,够本了,不治了,癌了还治,不过是自己和亲人们的自我安慰,到头来人财两空。师弟武铁柱癌了切,切了化,不到一年就走了。花钱遭那个洋罪,傻子!爷爷没给大夫回话,就离开了医院。这工夫,他的几个徒弟正在松花江上喊着,师父!杨师父!刚才他的手机响爆了,他也没听见。他给大徒弟打了电话,说自己已经在火车上了。大徒弟一听也不叫师父了,厉声质问他,往后你还上不上俺家来了?反正你家我是高低不去了!爷爷只好撒谎,说最好的一个一块儿游泳的朋友就要咽气了,他儿子打来电话,说他爹说啥也要最后见他一面。徒弟们这才稍稍消了火。师父从来不说假话。师父最讲义气。
车窗外一片白,没有一点儿别的颜色,一流水儿地向车后甩去。几十年,爷爷看惯了火车上跑动的北国风光,清清静静,顺顺溜溜,现在看来,有了别样的滋味。他本想从医院返回大徒弟家,说好了的,好不容易来一回,在H城多住几天,说话得算数。可人家是大喜日子,自己再忍再装,病就在那儿明摆着,能一点不露馅儿?大徒弟是个心细的人。别的不说,再喝,喝不喝了?昨天一杯不落,今天一口不动,这不给人家添堵吗?他也想了,病就这样了,照旧喝,病死也不能让它吓死。临走时把病情和大徒弟直说了——大徒弟比儿子还能拿事。可那样,自己就甭想跑了,就地被捺进医院……唉,多好的事,肠子就这么不给自己助脸,他曾多少回在徒弟们面前夸耀自己是钢筋铁骨,鼓励他们要向他看齐,活出质量来……现在爷爷想好了,病的事,除了老伴儿,谁也不告诉。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一根头发丝儿也不能藏着掖着。到家就和老伴儿过话,这么大的事,俩人担着心里会松快些。可他立马又变了卦,老伴儿也先不告诉了。这半年,老伴儿总说这样的话:谁先走谁享福,谁后走谁遭罪。他烦老伴儿这些话,才多大岁数,就说这些丧气的话。大前天,老伴儿攥着他的手对他下命令,必须我先走,你后走!听见没有?他哈哈大笑。笑什么!老伴儿一本正经地喊,答应我!他笑着回答,行,保证完成任务!严肃点!老伴儿又喊。他懂老伴儿,老伴儿超级爱干净,是家里外头都公认的,比如她去买肉,总先去各个肉店巡视一番,看卖肉人的指甲盖儿长不长,看他们打外面回来洗不洗手。不符合她条件的,肉再好,价格再便宜也不买。攥着他的手下命令那天,她是刚探望五婶回来,一句话絮叨了好几遍:人年轻时多干净,老了就多埋汰。五婶也是超级爱干净的人。老伴儿那天像变了一个人,又絮叨孩子:娘养儿,能养一帮;儿养娘,十个儿子也别指望。她装老的衣服早就自己做好了,做好后又洗又熨,板板正正挂到柜子里……她命令他,是让他必须干净体面地送她走。如果现在告诉了她自己的病,她会当场晕倒……
爷爷想开车窗,半天没打开,窗户被冻住了。终于打开了,他从怀里薅出那张CT片甩了出去。关上窗户,他回头见对面的年轻人正瞪他,心想年轻轻的咋这么不理解人呢?他坐下片刻就检讨了自己,大冬天的,孩子没错。
妈的,这癌咋瞄上我了哪?他心里骂,要是老伴儿一起去了H城,也看了松花江,这事绝对不会发生,她是不会让他迈进医院一步的……
回到家,爷爷不敢看老伴儿,就像在外边做了天大的缺德事。好在她没发现。孙子毛毛靠在他身上一动不动,他知道他是怕他再走。他和毛毛一起去铁道东看黑黑。这两天毛毛照顾着黑黑。黑黑“呜呜”着不停地围着他转,舔了他的左手舔右手,让他想起H城认真瞧病的大夫。他突然感觉它知道了他的病情。
当天夜里爷爷做了恶梦,梦见自己的肠子全黑了,像一根根黑烟囱,突然爆炸了,从肚子里崩了出来。他大声喊叫,惊醒了老伴儿。
“大山,你怎么了?”老伴儿惊坐起问,“喊啥呀?”
“我做梦了,”他也坐了起来,想了想说,“……我,我梦见,一只狼要吃我。”
“胡诌八扯的!快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