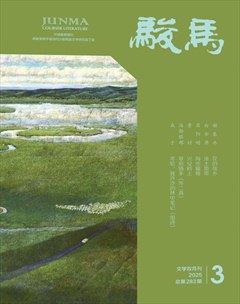一
生物实验楼的走廊总是安静的。即使在人来人往的课间,这里也像是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安静。苏羽第一次去标本室时,阳光正从高处的气窗斜斜地照进来,在米白色的地面上投下一道道光格。她记得那是个周四的下午,走廊尽头传来空调运转的细微声响,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福尔马林的气味。
标本室的门略微有些老旧,黄铜门把手上的漆已经剥落了一些。她迟疑了一下,才轻轻推开门。房间比想象中要大,四周的墙壁都是深褐色的木质展示柜,玻璃柜门后整齐地排列着数不清的标本。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斜射进来,在玻璃表面形成细碎的光斑。
第一次见到那只凤蝶是在右侧第三个展示柜里。那是一只已经死去多时的柑橘凤蝶,被固定在玻璃标本盒中,翅膀完美地展开,黑色的底色上装饰着优雅的黄色条带,尾部的凤尾格外修长。标本盒的一角贴着一张泛黄的标签,上面工整地写着——采集时间:2023年5月18日;地点:武夷山北区柑橘林;采集者:陈笛。
她站在那里,被这种近乎永恒的美丽吸引。展示柜的玻璃极其干净,她甚至能在上面看到自己模糊的倒影: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手里还抱着一本《昆虫分类学》。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实验室里的仪器和玻璃器皿反射着夕阳的光芒,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当她转身时,看见了陈笛教授。他穿着略显泛黄的白大褂,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比她想象中要年轻得多。微卷的黑发下是一张温和的面孔,说话时习惯性地推一下眼镜,这个小动作让他显得既严谨又亲切。
“这是去年在武夷山采集的,”他走到展示柜前,声音轻柔得仿佛怕惊扰了什么一样,“那里是凤蝶的重要栖息地。你对蝴蝶感兴趣?”
小羽点点头:“我在查资料时看到实验室有蝶类标本,就想来看看,”她停顿了一下,“没想到会这么美。”
陈教授笑了:“每个人第一次看到这些标本时,都会被它们的美震撼。但真正打动人的,是它们活着时的样子。”他转身走向办公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厚实的笔记本,“要看看野外考察的照片吗?”
那是她大二的第一堂实验课。陈教授带领学生们研究中国特有的蝶类分布与保护。他翻开笔记本,里面不仅有照片,还有密密麻麻的观察记录。每张照片旁边都标注着详细的信息:温度、湿度、海拔、植被状况。小羽注意到,每当他谈论蝴蝶时,眼神里都带着一种特殊的专注,仿佛在讲述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二
“每一种蝴蝶都与特定的寄主植物共生,”他解释道,手指轻轻拂过玻璃标本盒,“就像一段无法分离的缘分。柑橘凤蝶的幼虫以芸香科植物为食,特别喜欢柑橘类的嫩叶,这种共生关系已经持续了数百万年。大自然的奥妙,往往就藏在这些微妙的联系中。”
标本室的角落里有一台老式留声机,深褐色的木质外壳泛着温润的光泽。据研究生学姐说,那是陈教授的父亲留下的。有时候,他整理标本时,会放一些古典音乐。舒伯特的《蝴蝶》钢琴曲是他最喜欢的一首,那轻快的琴声在安静的标本室里回荡,仿佛真有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
从那天起,小羽开始频繁去实验室。起初是为了完成课题,后来却变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习惯。陈教授总是在那里,有时在整理标本,有时在查阅文献。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整齐有序,右上角放着一个青花瓷茶杯,里面的茶水总是半满的。
有一次,她在整理资料时不小心碰倒了一摞书。陈教授帮她捡起散落的纸张,发现其中夹着一首李商隐的诗。“你喜欢《锦瑟》?”他问道。那是她随手抄下的,为了记住某个突然想到的点子。
“嗯,”她有些不好意思,“特别喜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两句。”
“有意思,”他推了推眼镜,“我喜欢顾城。特别是《门前》,短短几行字就把大自然最本真的状态描绘出来了。‘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就像我们观察的这些蝴蝶,都在安静地完成着生命中最美的过程。”
春天的实验室总是特别忙碌。陈教授要准备新一轮的野外考察,还要指导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但每当小羽来实验室,他总会抽出时间和她聊天。从蝴蝶聊到诗词,从科学聊到传统文化。她渐渐发现,在这个总是穿着白大褂的教授身上,学术的严谨和人文的温度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有一个下午,实验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窗外下着细雨,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特有的湿润气息。陈教授正在摆弄显微镜,突然说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候条件很艰苦,”他说,“但每次看到新的物种,那种兴奋感至今难忘。现在的学生们,有更好的设备,更广阔的视野,但不知道还能否保持那种纯粹的热爱。”
小羽站在窗边,看着雨滴划过玻璃窗。她想说自己也有那种纯粹的热爱,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教授,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蝴蝶?”
陈教授放下手中的工作,眼神有些恍惚:“也许是因为它们太美了。美到让人想要去了解,去保护。每一种蝴蝶的消失,都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损失。”他看向窗外,“就像现在这样的春雨,滋润着万物生长,而蝴蝶就是大自然最好的使者。”
春天悄然离去,五月的风已经带来了夏天的气息。那天下午,阳光格外明媚,陈教授在整理野外考察的装备时,突然抬头问她:“要不要去武夷山?我们要去观察夏季蝶类活动,那里的生态系统非常完整。”
三
她立刻就答应了,仿佛期待这个邀请已久。后来她才知道,这次野外考察原本只计划带研究生,是陈教授特意为她申请了名额。
考察队一共有四个人:陈教授、小羽,还有两名研究生。张露是研三的学姐,专门研究蝶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李斯是研二的师兄,负责生态环境调查。他们都有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对小羽这个“新手”照顾有加。
考察开始前一周,陈教授组织了一次周密的准备会。张露展示了她收集的武夷山近五年的气候数据,指出五月中旬是观察凤蝶最理想的时节。李斯则根据卫星地图,标注出几处凤蝶可能存在的栖息地。小羽负责整理采集工具,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每个器具的完整性。“去年这个季节,我在北区发现了一片新的柑橘林,”张露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点说,“那里的环境特别适合柑橘凤蝶繁殖。”她说这话时看了看陈教授,后者微微点头。
李斯补充道:“最近几年山里的开发项目增多,要抓紧做生态调查。”他翻开笔记本,“我建议这次重点关注环境变化对蝶类栖息地的影响。”陈教授认真听着他们的汇报,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阳光斜照在他的镜片上,映出一道淡淡的光晕。
小羽坐在一旁,默默地记着笔记。她注意到陈教授在提到某些观察点时,语气会变得特别柔和,仿佛在谈论一个珍贵的老朋友。
考察开始于五月中旬,那时武夷山的天气正好,不冷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