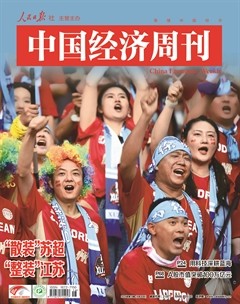近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着眼于提高城市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承载能力,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
这一重要部署,不仅明确了下一阶段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方向,也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迈入新阶段,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
19个城市群承载全国70%以上的人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稳步推进城市群建设。截至目前,已规划建设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长江中游、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滇中、宁夏沿黄、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0%以上的人口,贡献了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成绩值得肯定,问题也不容回避。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城市群更注重城市间的分工、联系与互动,而都市圈则更强调中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多个城市群和都市圈,但大多数城市群内部联系仍不够紧密。同时,不少都市圈范围偏大,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往往仅限于圈内核心区域,难以有效带动外围地区发展。
“除个别案例外,无论是城市群还是都市圈,目前总体上仍处于发展阶段,距离成熟形态还有差距。”李国平说。
多年来,传统“摊大饼”式的规模扩张,导致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与资源承载压力加剧。这种发展模式促使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不断向中心城市聚集,进而引发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典型城市问题。中心城市辐射不到所有区域,一些省际毗邻区就沦为发展洼地。
“如果能够在中心城市下面形成‘县城—小城镇—乡村’三级节点网络,辐射能力就会极大增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对本刊记者说。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提供的一组数据进一步佐证了上述观点:
当前大多数城市群中,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各类生产要素的有效联系和辐射半径普遍不超过100~150公里,覆盖面积约在2万至3万平方公里,与最初设想的8万~10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群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此外,不少规划中的城市群其中心城市本身仍“发育不良”,尚处于“强省会”的建设阶段,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这意味着,在优化现代城市体系的过程中,需进一步强化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协同,增强中心城市对外围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这也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要义。”孙久文说。
平衡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功能分工
李国平这样理解“组团式”“网络化”的内涵。
“组团式”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发展模式,强调城市功能在布局过程中应避免“摊大饼”,转而通过相对独立又功能互补的组团推进城市扩张与布局,引导城市形成多中心结构。
“网络化”是指通过高效互联的基础设施,打通各组团乃至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联系,保障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顺畅流动与共享,推动一体化发展,最终构建一个环境宜居、运行高效的城市群或城市有机整体。
“‘组团式、网络化’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也体现出对优化城市体系格局与形态的长期坚持。”李国平说。
在孙久文看来,“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模式,是中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创新。
“这一模式旨在应对传统单中心城市模式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核心城区的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环境恶化等典型‘大城市病’,以及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中小城市承接功能外溢困难等结构性矛盾。”孙久文说。
目前,我国大城市数量较多、规模也不小,从发展趋势看,李国平认为大城市的数量还将继续增加。
“大城市基础设施更为完善,吸引力更强,人口仍在持续向大城市集中,较少流向中小城市。未来中小城市收缩的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关键在于推动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与协同发展。”李国平说。
平衡核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功能分工,是组团式网络化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挑战,需要通过产业协同、要素配置、制度创新、设施联通等多维度系统性设计来实现。
孙久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首先,从过去注重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地协调为导向的新范式。核心城市聚焦高端产业,如总部经济、研发设计、金融贸易和国际交往等功能;一般制造业、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非核心功能则有序疏解至周边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可依托专业化定位,建设成为制造业基地;县域地区则应重点承载农业、绿色食品加工、旅游和康养等特色产业。
其次要构建要素双向流动的通道,既允许中小城市和县域人口流向中心城市,也鼓励核心城市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和县域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