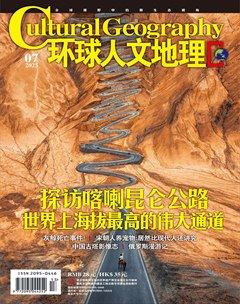西汉长安城的始建,只是从长乐、未央两座宫殿开始,谈不上城市结构。皇权的概念仅仅体现在未央宫自身的壮丽,而不是城市的整体形态。城市整体(包括宫殿和各类居住区)是存在的,但在空间结构上主要是自然发展,没有被规划或赋予具有高尚意义的准则。
长乐、未央两座宫殿形成职能核心区,两宫之间所夹的南北通道,在实际活动中具有中心意味。北面增修的宫殿,自然从方位关系上命名为“北宫”。长乐、未央、北宫3大宫殿群,确定了刘邦长安的核心地带,其间还有具备防范功能的武库。武库的修建完全是出于实际功能的需要,不具备意识形态意义。宫殿北面与渭河所夹地区是大面积的居民区、市场区以及其他功能区。上述就是刘邦修建长乐宫以后10年间的城市形态。
公元前192年,汉惠帝开始在长安周围加筑城墙,这项工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完全出于实用考虑。不过,城墙的出现毕竟确定了一道界线,可能有一些功能区受到影响,需要重新安置调整,例如,新起的西市被整齐地规划在长安城墙内。在城墙范围之内,宫殿北面直到北城墙的区域,应为居民区。
在初期的长安城,城市生活重心在北部,并注重与渭河北岸的关系。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三辅旧事》等文献中的说法,初期的长安城之所以重视与渭北的关系,是受秦朝旧咸阳城格局的影响。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对于渭水河道运输功能的实用考虑,是“取其便也”。未央宫虽然坐北朝南,但实用起来,却是北部繁忙,所以要建北阙;南部萧条,没有建阙的必要。宫殿的门阙,要面对活动人群才有意义。
长安城的实际生活是朝北的,是朝向渭河谷地的,而南部是内区,是后方。另外,匈奴的威胁也来自北方,所以长安周边的军事防守也只是守东、西、北3面,没有南面。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礼制建筑在长安城的南部出现,就意识形态意义来说,南部逐渐重于北部。
武帝以前,长安只有3组宫殿:长乐、未央、北宫。而武帝基于王朝的繁盛和自己对宫殿作用的重视,大力增筑新宫殿,主要有桂宫、明光宫、建章宫,令长安宫殿占地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相应地,长安城围墙范围内的居民区则大幅度减小。
在武帝看来,宫殿比城市更重要,建章宫与明光宫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城墙的否定。庞大的建章宫可以无视城墙界线的存在而坐落在西城墙的外边,建章与未央之间,有阁道跨越城墙相联通。明光宫的修建,必然将大面积的居民迁到城墙之外,这也否定了城墙的分隔意义。建章宫的修建,起因是要起“大屋”,以方术之法去镇胜火灾,但实际修建出来的宫殿,却是在满足皇帝的奢华欲望和对仙境的模仿,似乎与朝政没有关系,所以后来王莽在营造更加符合儒家礼制化的京师时,将其拆除。
武帝没有像秦始皇那样提出对都城总格局的构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武帝缺乏对象征意义的追求。除了模仿方士们宣扬的海中山、神明台以外,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武帝曾有在长安城南建立明堂的计划。这是一项儒家礼制建筑规划,可能是长安城第一座有意体现儒家思想的建筑。由于这座纯粹的意识形态建筑选址于城南,将赋予原来缺乏都城重要内容的长安之南异乎寻常的意义。不过,《史记》《汉书》中都没有武帝的明堂在长安修建或完工的记载。
武帝是一位具有高度意识形态信仰的皇帝,但当时一些重要的王朝信仰活动并没有汇聚在都城,在都城的景观建设上,也没有充分展现这些信仰活动的内容。汉武帝的礼仪空间视野宽广,很重要的一些祭祀,如雍畤、后土、泰一等都不在长安,不少祭祀活动场所未能脱离实际的山川场地(如封禅)。对比后来形成的都城郊祀(重要的祭祀活动收缩在都城近郊),武帝的祭祀活动空间几乎覆盖了整个帝国。对于武帝来说,作为场所的都城属于皇帝,不属于神祗,至少不是神祗的重要场所。都城主要是皇帝居住、施政,以及展现自己威仪的权力之地,所以宫殿是最重要的,其余的寰宇山河信仰均表达在都城范畴之外。在这种情形下,都城体制即宫室体制,都城并没有多少超越宫室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