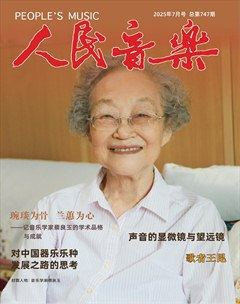谓“跨文化"(Cross-Cultural)是指不同文化背景所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发生的互动与交流的过程。它关注的核心是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在接触时产生的碰撞、理解与融合,它涉及人类社会诸多领域。地域性民间音乐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越是多民族集聚的地区,越能够相对完好地保存其民间音乐文化的独特性和风格性,其“原生性"和“本真性"的保存相对完好,即所谓“地道”。作为以生存技艺而存在的传统音乐文化与当地各民族人民生存的息息相关,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常常挂在嘴边的“艺术"现象。青海作为多民族集聚的省份,其境内汉族、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多民族交融混居,和睦相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工商业文化融合共促,使其呈现出“多元互融”特色鲜明、风格独具的民间音乐文化格局。
之所以选择“琴音倾城绕长风一中国风格钢琴作品音乐会”这样一次“跨文化"对话与交流活动①作为解读对象,正是基于“跨文化"的观念和实践方式在特定地域所带来的现实成果。外国钢琴家演绎中国民间风格的钢琴作品,类似的表演实践现象并不罕见,但对于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而言,却着实具有某种开先河之意味。从艺术观念来看,“民间音乐”与“艺术音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分属两个不同领域;“艺术音乐"的哲学基础是“个体本质”观念,“民间音乐”的哲学基础则是“集体本质”观念,当两者融合为新质构成以后,原初的观念和意义随之发生改变。从演绎的意义生成角度来看,当跨文化理解与阐释成为可能的那一刻起,创意表达被这种可能性重新建构为一种新的意义场域,使得跨文化对话的预期价值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地域、民俗、符号
作为地域性音乐文化,它指向了某一特定地域的人及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场景和人文创设景观,构成了特定地域下人们的生存现实与场景。“地域性民间音乐文化符号”是这场“跨文化"对话的专属创意之一,它是介于生活观念和艺术观念之间的融通。将不同民族的民俗生活歌谣、歌舞以“钢琴作品"的方式加以呈现,它指向了特殊人群、特定地域、特定文化符号的特殊存在方式。通过这种“局内人”预设和“局外人”阐释的演绎过程,把“局内人"的感受和体验与“局外人"的解读和阐释融为一体,由此建构“钢琴作品”与“民间音乐”之间跨文化的新质构成关系。
从作品标题可以看出,《登呀登》是汉族小调,由衬词“登呀登"而得名;《打墙歌》是藏族劳动号子加弹唱;《安昭舞》是土族逢年过节或婚礼喜庆活动时的一种歌舞表现形式;《巴西古溜溜》是传统的撒拉族民歌,以句首撒拉语“巴西古溜溜"(意为圆圆的头)命名;《小黑马》蒙古族长调民歌,是一首情感真挚的情歌。当诞生于青海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工商业文化融合观念下的民俗歌谣、歌舞,以“艺术观念"被赋予独特的纯粹声音的表现形式时,语言的语义指向性便由其所指转变为能指,原有语言语义本身的所指就此失去意义,这种超越语义的声音表达更多体现为一种音响感性特征的直接性。钢琴作为纯音乐体裁的独奏乐器,正是西方社会“个体本质"观念的具体体现,这一观念在今天国人的观念中早已落地生根,说明"西乐东渐"百余年来跨文化交流对话与理解阐释所生发的结果。从整体来看,“个人主义"(个体本质)和“集体主义"(集体本质)这两个维度描述了一个社会所强调的不同目标。在西方个体本质的文化中,个体自由、独立和自我实现被高度重视;在东方集体本质的文化中,社会和谐、群体利益和共同目标则占据中心地位。可以确定的是,“‘集体本质观念’正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农耕文明环境下孕育而生的本质特征,它对应的是有着时空界限和文化界限以及不同社会基础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特殊存在"②。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将单一观念和单一思维整合为一种整体发展观。“任何一种音乐都与它那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有着最密切的关系。音乐是语言在情感、音调和节奏方面的延伸和深化。"从地域、民俗、符号三者的关系来看,能够将其连接在一起的决定性因素即语言,然而当其以超越语义的纯音乐的声音方式加以表现时,它将为演绎者(或欣赏者)预留了新的解读和表达的自由空间。
如果换一种方式,不是视觉优先,而是通过一种声音去感受和体验过往的生活经历,结果又会如何呢?纯音乐声音结构的隐喻方式,一定会将地域、民俗、符号所表现的有限性加以拓展和延伸,正如今天中国人对钢琴音乐的接受和理解已无法同百年前的语境相提并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