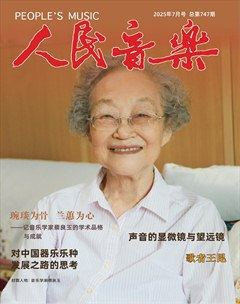世界文化交融逐日加深的背景下,探寻“中国在文化本位”是文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作曲家也在不断思考如何在音乐创作中体现“中国性”。协奏曲作为源自西方的大型器乐体裁,自2O世纪进入中国后逐渐成为中国作曲家重要的创作领域。经过在这一领域近七十年的深耕,作曲家们令民乐协奏曲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协奏曲的新面貌。作为听众,我们在聆听民乐协奏曲时对其有何期待?一方面是从协奏曲原本的体裁特性出发,品味独奏与乐队的互动,品鉴独奏家的炫技;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编制上民乐器的加入而期待新的音响效果。但更为深层的是,民族乐器如何在这一源于西方的音乐体裁上表达“中国声音"?如何吸纳、消化和表达传统文化?笔者在此以“海上新梦·十六"①上演的八部青年作曲家的原创作品为例,从传统艺术体裁与协奏曲的融合、独奏民乐器个性的呈现,以及独奏民乐器与交响乐队音响关系的处理三个维度观察青年作曲家们如何让协奏曲"说中国话”。
一、旧“曲”再奏,古韵新“生”:传统戏曲与协奏曲的融会贯通
作曲家在创作具有民族性的作品时大多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本场音乐会的作品同样与传统文化密切关联:或是以古诗词内容作为作品架构的原则,或是以古曲旋律作为主题发展线索,或是再现民俗民风之场景,又或是表达中国传统意象…笔者以为,其中由武越(广西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创作的唢呐协奏曲《满腔》(2023)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戏曲文化,更是将这种传统文化与协奏曲的体裁特性融会贯通:作品通过对京剧行当的刻画令唢呐的个性得到多维度挖掘,同时交响乐队的编制也给戏曲的表现带来更大的张力。
作品采用板式一变速的结构思维,除引子与尾声外,分别以四个段落刻画丑、旦、生、净四个行当,并根据行当的特点设计不同的速度:第一部分小快板,如同丑角诙谐轻快的步伐;第二部分行板,似是青衣娓娓道来;第三部分快板,犹如短打武生轻捷矫健的身姿;第四部分慢板,展现净角的稳重大气。同时,这四个段落正好形成西皮一二黄一西皮一二黄的结构布局②。
独奏唢呐担任了这四个行当的唱腔部分,旋律设计贴合了不同的唱腔特点:插科打浑的丑角重“念”,且念白偏口语化,因此旋律是碎片化的,节奏自由多变犹如说话时的抑扬顿挫,甚至有笑声的模拟;庄重抒情的青衣唱功繁复,故而唢呐演奏完整的旋律;武生重“打”,因而旋律需配合其动作而要求干净利索;净角动作大开大合,故而旋律雄浑凝重。除此之外,唢呐演奏家刘雯雯对不同行当的润腔与音色处理更是为这部作品锦上添花:青衣细腻委婉,故而音色柔和并有频繁的润腔;武生轻捷矫健、干净利落,故而较少润腔。这一细节处理令独奏乐器更具有“人性”,京剧角儿的形象在器乐体裁上栩栩如生。
乐队则负责不同行当的动作与气氛渲染。为了使作品更有“京剧味儿”,乐队中加入了京剧常用的打击乐器,结合不同行当的动作特点加以配合。板鼓、小京锣、饶钣、郴子等戏曲打击乐器与弦乐拨弦的谐谑性音调表示丑角粉墨登场,打击乐器之间的频繁互动犹如丑角抓耳挠腮、扭腰挥臂等滑稽动作;而青衣行动稳重,动作幅度较小,因此极少使用打击乐。描写武生的段落最为浓墨重彩,打击乐器几乎全部上场。先以一段紧锣密鼓的武场过门预示武生登场,随后便是一段精彩的板鼓与唢呐的互动:乐队厚重的音响突然褪去,只留下独奏唢呐与板鼓的对话,听众的注意力此时只聚焦于两者,简洁利落的配器凸显了武生跌扑翻打的“漂、率、脆”。净角则以慢起渐快的旋律登场,打击乐也跟随其逐渐热闹起来。
当然,在协奏曲中融入传统戏曲元素的做法并不新鲜,此前已有权吉浩的琵琶协奏曲《京剧印象》(2005)和贾达群的民族器乐协奏套曲《梨园》(2019)等优秀先例。珠玉在前,既为后人起到标杆作用,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艺术重压。于笔者而言,《满腔》对传统文化开门见山式的呈现实属难能可贵:作品并不故弄玄虚、曲高和寡,听众们在音响中能够轻易地捕捉到不同角儿的“亮相"和“唱念做打”,以及“东方赞"“急急风”等熟悉的影子,从而使作品能够在亲切的敲锣打鼓声中拉近与听众的距离,传统文化的魅力不言而喻。
二、多元并存,不拘一格:独奏民乐器个性的传承与开拓
独奏乐器个性的呈现是协奏曲重要的体裁特性。置于民乐协奏曲的语境中,独奏民乐器与生俱来的鲜明个性应当如何处理是作曲家首要思考的艺术问题。就本场音乐会而言,大多数作品保留了独奏民乐器的原生个性,以符合作品所要表现的标题内容。巧妙的是,这些独奏民乐器的天然性情与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在寓意和气质上合而为一:唢呐既可以雄浑激昂的音色渲染戏曲的热闹气氛,又可以百转千回的曲调模拟“角儿"的唱腔;“笙”通“生”,寓意万物生发,犹如寒青生机盎然;古筝清澈透亮的音色既可表现水光瀲滟,又可比拟荷“出淤泥而不染”;竹笛生于竹,竹亦有“清华其外、淡泊其中"之寓意,清脆悠扬的笛声似是传达“漱石枕流"式的处世态度。③
二胡以婉转低回、如泣如诉的音色特征见长,林虎(中国音乐学院在读博士)在《青山之恋》(为二胡和管弦乐队而作,2023)中将这种音色特征与巫山神女的形象紧密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