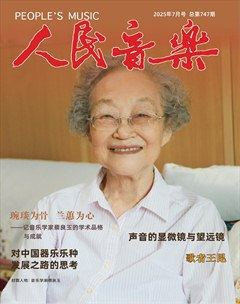2025年6月7日,当唢呐演奏家张倩渊手持亚美尼亚嘟嘟克吹响《苍吟》的第一个长音时,原本热闹的音乐厅里立刻安静了下来。这件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在一位年轻的中国唢呐演奏家的吐纳间流淌出苍茫的丝路叙事一使得这场音乐会更像是一次文化基因的交汇与解码。作为唢呐界唯一的“金钟奖”“文华奖”双料金奖得主,张倩渊以“丝路唢呐”为名,在6月初分别于成都、西安的舞台上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丝路音乐之旅:她手中的唢呐时而化身波斯商队的驼铃(《塔赫特随想》),时而变作贵州山野的歌谣(《树魂》),时而又熔铸成电子脉冲中的京韵(《朝锣暮鼓》)。而这场声音行旅,恰是一位年轻民乐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宏大命题的探索和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亲历与践行。
一、声学地图:唢呐作为丝路文明传播的载体与见证
节目单上第一首作品《海上丝路》(吹打乐)热烈的奏响,其间暗含一份历史隐喻:作为一件丝路文化的“舶来品”(其波斯原型“苏尔奈”经陆上丝路传入),在当代作曲家的创作中,经由三支唢呐奏响“海上丝路”的波涛涌动,并在汇流的过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华化”①与融合。
音乐会的第二首作品《苍吟》,根据音乐会节目单上的表述,此为“世界音乐”,所演奏乐器是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外高加索南麓的亚美尼亚的“嘟嘟克”。据张倩渊介绍,这支“嘟嘟克”是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演出时向当地演奏家购入的。与开场第一首《海上丝路》的热烈与激情不同,这首作品就像它的名称一样:如一阵悠远的吟诵,源自古老、苍凉的过去。张倩渊手中的“嘟嘟克”外形与我国的“管子”颇有几分相似,音色也与管子接近,暗淡悠远的声音让人听了很容易就安静下来,并陷入思索。在演奏中,张倩渊用中国管子的“循环呼吸法”激活了这件千年古木,那段令人室息的持续低音,正是利用管子演奏的“喉音技巧”拓展了嘟嘟克的传统表现域;而听众们则仿佛跟着音乐会在漫长古老的“丝路”古道上游走,体会一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的纵深感。
像前两首作品这样,基于丝路的文化交融并进一步呈现文化反哺现象,则在音乐会的另一首作品《塔赫特随想》中被进一步放大。这部作品由两件不同地域的“唢呐”,即埃及唢呐(Mizmar)与波斯唢呐(Sorna)并置,并通过在音乐律制与节奏方面的复合与碰撞,还原了丝绸之路作为“音律大熔炉”的场景。在演奏中,这部《塔赫特随想》在音律和节奏等方面变化丰富,具有鲜明的异域风情特征,既是作品的特殊之处,也给演奏带来一定的难度,作品中间一段打击乐solo也很精彩。此作品之后,是由陕西青年唢呐演奏家冯苗苗带来的《高粱熟了红满天》改编自阿鲲的影视音乐《九儿》,在新的编创下具有流行音乐风格,近年深受群众喜爱。音乐会中这样的安排,也将悠远的西域丝路拉回苍劲荒凉的中国西北高原。
上半场最后一支乐曲,张倩渊演奏了具有贵州少数民族风格的双唢呐作品《树魂》。此曲由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家、民乐指挥家朱晓谷先生于2006年创作。作品一开始,两支唢呐以交替的呼唤和回应,将音乐逐步带入林木茂密的西南高原,仿佛先民们面对大山和苍天的一声声高亢的长啸。其中的双唢呐配置,以带有“句句双”特征的双重主题和复风格写作,以高音唢呐模拟贵州苗岭“飞歌”般的滑音,另一支次中音唢呐则演绎侗族大歌的持续低音。而“气冲音”的技法则奏出仿佛贵州雷公山的松涛声,并在打击乐铿锵的节奏映衬下,使音乐呈现出一份独特的原始、古朴气息。该作品展现了西南民众特有的“在节日、祭祀中围绕神树载歌载舞的文化景观”③,与之前的“红高粱”的西北风形成鲜明对比。
下半场的作品以近现代经典民族器乐合奏作品《金蛇狂舞》开场,在聂耳原作的基础上,青年作曲家苏潇进行了恰到好处的编创,于前奏的引入和铺垫及中间的和声配置等方面,都有很多新的发展,同时也很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风貌和气质,并以此给张倩渊的演奏带来更为丰富的表现空间。随后,则是具有浓郁京味风格的《朝锣暮鼓》。作为一首由电声录音伴奏的作品,此曲呈现出一份特殊的时尚气息,也再一次印证了唢呐这件乐器,有着极为丰富且多元的表现力和多重面向的形象空间一可以是很民间的,甚至“土的掉渣儿”,也可以是很时尚的,走在“潮流'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