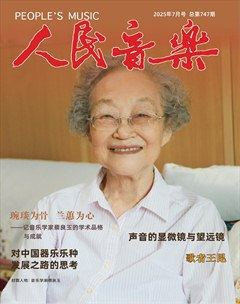23年6月与2024年11月,文化和旅游20 部分别在河北廊坊、江苏无锡举办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民族器乐展演”,每届都有超过三十个乐种参加展演。笔者在观看第一届演出后,曾撰文《路在何方?一对中国器乐乐种发展的思考》①,探讨乐种舞台化后的问题及新组合在未来发展的中作用。第二届展演中,各地方乐种的呈现既强化了我此前的思考,又催生新想法,在此与大家商讨。
一、中国民族器乐合奏的四种类型
音乐学界对“乐种”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其一是指器乐合奏种类,等同于“歌种”(民歌)、“剧种”(戏曲)“曲种”(说唱)“舞种”(舞蹈);其二是袁静芳老师所提出的“乐种学”概念,是指历史传承下来的,具有大型结构特征的,用于民间、寺庙等不同场域的器乐与声乐类型。之所以有声乐,主要原因是有些乐种包含声乐部分,如福建南音。可见,“乐种”并非一个内涵清晰的概念,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情况复杂多样,采用民歌、戏曲、说唱、歌舞、器乐的分类方法不能够涵盖民间音乐实践的复杂情况。
“全国民族器乐展演”中所用“乐种"概念,主要相对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大型交响化乐队)而言,指代传统音乐元素与风格的小型组合,既包括民间传统器乐组合,也包括新成立的、以演奏传统音乐风格的乐曲为主的器乐组合。从两届展演看,民间传统组合减少,新组合渐增:有些新组合演奏传统曲目(如中国音乐学院“国音雅韵组合"的潮州弦诗乐《雁南归》和《福德祠》),有些演奏新创曲目(如无锡市民族乐团“清泉丝韵组合"的《丝竹今生》),还有对传统曲目进行重新编配(如枣庄鲁南软弓京胡组合的《百鸟朝凤》、云南耿马“布果傣乐组合"的《拟声菠萝鼓》)。总体呈现民间组合少、专业院团组合多,传统乐曲少、改编与新创曲目多的趋势。悄然中,乐种在发生着变化。由于这些专业化的新组合是传统乐种的延伸,并不能构成“新乐种”,在此把它们称之为“新组合”,而来自民间的组合形式则称之为“传统组合”。“民族器乐室内乐"因以演奏当代创作作品为主,不被纳入到乐种范畴。由此,在民族器乐合奏中,便形成了如下四种类型:民族管弦乐队(民族乐团)乐种的“传统组合”乐种的“新组合"和民族器乐室内乐。前三者均在“中国民族器乐展演”中呈现。
二、乐种“新组合”对中国传统器乐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组合在民间传承面临困境,“非遗”保护虽有助力但难保障延续,而新组合为乐种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正如第二届展演研讨会上张振涛老师所言,“乐种在学院的传承是保证传统音乐能够传承下去的有效途径”。综观这些“新组合”的演奏,我们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其一,队员职业化。传统乐种多为民间器乐组合,而新组合多由院校或院团职业演奏家构成。第二届展演中,来自学院的组合有9个(含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菏泽学院、江苏省戏剧学校、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等),专业院团组合12个,民间组合10个(其中包括由当地文化部门建立的带有一定专业性的组合,如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的组合)。可见,学院与院团的专业背景组合占多数。以中国音乐学院“国音雅韵组合”为例,在王中山教授的引领下,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音乐,师生组成的团队每年邀请地方乐种专家授课,2023年演奏江南丝竹,2024年演奏潮州弦诗乐,技艺精湛且经专家调教,艺术表现力充分彰显。
其二,乐曲新编配。“新组合”往往会对传统乐曲进行新的编配,其中含三种情况:一是专业院校和院团组合对所演奏的传统乐曲均经历了“整理”的过程,虽力求“原汗原味”,但由于他们高超的演奏技术,使乐曲风格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是来自民间的“半专业组合"对传统音乐的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