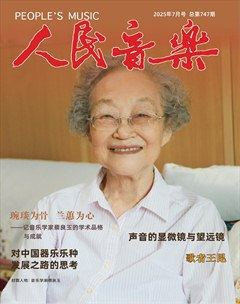由樊祖荫口述,马学文、欧阳平方记录,樊荣整理的《我的音乐人生一樊祖荫口述》以平实的语言回溯其学术生涯,书中不仅清晰勾勒出与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变化同频的轨迹,更映射出他六十余载时光里在中华音乐文化的浩瀚时空中,一步一个脚印执着探索的历程。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形成了敏锐的问题意识,在理论和实践交织的耕耘中不断突破,最终成长为集作曲、作曲技术理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事业领导者于一身的杰出音乐家,始终致力于搭建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桥梁。
樊先生这部口述实录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构建起八个核心主题。
一、“三个地方三所学校”,追述了他在浙江、上海、北京三地,于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的生活、求学与工作经历。1940年,樊祖荫出生于浙江余姚乡村一个寻
常人家,淳朴家风和江南民间音乐的熏染,塑造了他诚信坚毅的品格和求知爱乐的浓厚志趣。初中时,在音乐老师的启蒙下,他创作了多首歌曲并发表,由此萌生了追寻音乐的梦想。1956一1964年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本科作曲专业求学,不仅深耕作曲技术理论,专注中外和声学领域发展动向,还协助黎英海教授编撰《多声部音乐写作教程》。他牢记贺绿汀先生曾说的一句话—“广西民间合唱中非常好听的大二度是我们特有的音乐”,深入研究广西多声部民歌,并以《广西多声部民歌规律初探》作为毕业论文,由此开启了他对中国多声部民歌的探索之路。1964年,他随黎英海教授调入初建的中国音乐学院,次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73年,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合并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1978年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1980年,他调回复建的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工作的前16年,尽管经历了动荡生活,但他初心不改,始终坚持中国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自1980年起,他迎来学术高产期,即便担任行政与专业领导职务,直至退休仍笔耕不辍,完成诸多开创性研究成果,培养出大批音乐领域精英人才。
二、“好什么呀,音都唱不齐!”该题出自20世纪80年代音乐界普遍存在中国民间是否有多声部音乐的怀疑或误读。樊先生讲述了他长期不懈地探寻各民族歌唱活动中所谓“唱不齐”的音乐形态的经历。他走遍中国大地踏勘,在民间音乐中细致观察,发现了中国有三十多个民族的音乐存在多声部音乐体裁及其自身表现形式的事实,证伪了中国缺少多声部音乐传统的陈说,完成了《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这部中国多声部音乐研究领域中具有拓荒性、基础性的学术成果,为发展中国风格的多声部音乐创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教学相长,和而不同一我的和声教学”,以丰富教学案例生动诠释了他在和声教学中形成的“和而不同”理念和实践。和声学教学与研究是樊先生音乐学术生涯的核心领域。面对中国和声教学长期依赖西方体系的状况,他致力于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并将其纳入和声学学科建设。通过教学中与学生积极互动,以问题为导向推进理论探索,力求让学生既掌握西方大小调功能和声的逻辑,又领悟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特质,努力构建中西交融的和声教学体系,培养出一批能够把握中国风格多声部音乐的作曲人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樊祖荫先生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期间,曾担任一个小班的和声课教学。针对该班学生“爱提问”的特点,他采用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充分备课、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取得显著效果。该班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或音乐理论家,如谭盾、陈其钢、陈怡、周龙、周勤如、瞿小松、陈远林等。①
四、“传承师学,继往开来一我的和声研究”,讲述了樊祖荫在黎英海教授《汉族调式及其和声》的学术指引下,对中国五声调式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历程。他耗时二十余年,系统分析中国作曲家的和声学实践,发表《中国和声学研究八十年》等多篇论文,并开展对马思聪、黄虎威、黎英海等作曲家和声写作特征的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