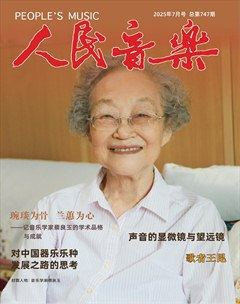场中地后多个权先后定都长安,留下了丰富的考古遗存。近年来,十六国乐确大量出土,为深入认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其中的歌唱俑尤为珍贵,为研究汉魏以来相和歌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可靠实物资料。
一、关中十六国出土歌唱俑
21世纪以来,关中地区已知出土十六国乐俑的墓葬有十余处,其中北贺墓地M298、坡刘墓地M2、布里墓地M63的歌唱俑格外引人注目。
2009年,咸阳北贺墓地M298出土了42件组合完整的珍贵乐俑,包括19件踞坐乐俑和23件立式俑。19件弱坐乐俑中,17件为乐器俑,2件为抃手俑。23件立式俑根据其发髻、服饰、尺寸等的差异,可分为13件和10件两组。体型较大的13件又可细分为两种,第一种共4件,为泥质黑陶立式俑;第二种共9件,为泥质红陶立式俑。二者在形神与发髻上似有男女差异。立式俑位于坐乐俑后方,推测其与踞坐乐俑构成歌唱与伴奏的关系。
2019年,在咸阳坡刘墓地M2出土15件乐俑。包括10件踢坐、立式乐器俑和5件立式俑。乐器俑手持吹、弹、击奏3类9种乐器。5件立式俑依据年龄、服饰分为1件和4件两组。这5件立式俑是否构成“一人唱,众人和”的唱和形式,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2022年,在咸阳布里墓地M63出土31件乐俑,包括20件踞坐乐俑和11件“姿态”俑。乐器俑手持吹、弹、击奏3类8种乐器;东、西两侧乐器俑中心的方毯上,有4位坐歌唱俑,手心相对,似随乐而动。四周7件立式俑神态各异:有的双手抱于腹部,双唇微张作歌唱状;有的昂首仰面,双臂上举,双唇张开作歌唱状。
北贺墓地M298乐确组合照

北贺墓地M298歌唱俑

三组乐俑的共同特征在于均包含歌唱元素。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歌唱的重要性长期被忽略,实则它在历史中占据核心地位,《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等文学形式均离不开歌唱。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音乐与文学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某种意义上,中国音乐文学史亦可视为一部歌唱史。
二、相和歌还是真人代歌?
十六国时期,汉魏以来的相和歌、相和大曲与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相互融合,逐渐成为“真人代歌”“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三处歌唱俑极可能与“真人代歌”有密切关系。
《魏书·乐志》记载:“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①据此可知,北魏政权为保存本族群历史,以长达150章的“真人代歌”记录了拓跋氏的兴起与发展。据“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②可知,真人代歌是一部总括十六国以来鲜卑各部胡乐,以及姚甚羌歌、苻秦氏歌等曲牌乐调的史歌。真人代歌与我国少数民族留存的长篇叙事诗有类似之处,除具备“上叙祖宗开基所由”等叙事记史的功能外,还承担“郊庙宴飨”的娱乐功能。
真人代歌于北魏最盛,其内容并不限于鲜卑拓跋部,亦兼有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事迹。例如《巨鹿公主》一篇来自羌族,“似是姚芸时歌”③,而后秦姚氏曾定都于长安;《企喻歌》源自氏族,前秦氏族亦建都长安。由此可见,真人代歌的许多内容与关中有密切的联系,上述三处歌唱俑或为真人代歌的表演场景再现。尤其北贺墓地M298抃手俑、歌唱俑与乐器俑共同构成宏大场面,值得重视。抃手俑与合唱俑同时出现在十六国乐俑中尚属首例,二者是领唱与合唱的关系,还是抃手俑参与合唱或承担击掌指挥职能,均有待深入研究。但无论哪种情形,都表明“抃手俑”与歌唱俑已出现分工,凸显出歌唱在表演中的重要性。
坡刘墓地M2前室乐俑组合照

真人代歌与相和歌关系密切,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借鉴、彼此吸收。相和歌盛行于汉魏时期,因使用丝竹乐器相和而得名。真人代歌原本是鼓吹乐,入乐府后始“与丝竹合奏”,其改编与演奏方式深受魏晋乐舞影响,表演形式也与之颇为相似。
另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③由此可见,真人代歌属于“鼓吹乐”的范畴。西安草场坡歌唱女俑与骑马鼓吹俑、立姿鼓吹俑同出,正是这一属性的真实反映。从“今存者五十三章”推测,真人代歌应为结构庞大的“鼓吹大曲”。草场坡M1十六国墓葬乐俑,似乎正是马上鼓吹乐与丝竹合奏在墓葬中的呈现;咸阳平陵M1的骑马鼓吹俑与坐姿鼓吹俑同时出现,可能分别表现墓主人居家宴乐和列队出行的场景。
布里墓地M63前室乐俑组合照

北贺墓地M298的23件立式歌唱俑存在性别、年龄差异;坡刘墓地M2的5件歌唱俑可按年龄分为1件和4件两组;布里墓地M63的歌唱俑则有踞坐与立式之分,这种差异或许是分声部演唱在队形中的体现。
三处墓地歌唱俑表现的可能都是真人代歌的表演场景,仅伴奏乐器和人数规模存在差异,这应该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有关。
真人代歌以记录鲜卑“开基所由”为主,据《通典·乐六》记载,唐代仍存真人代歌中的《企喻》篇,《企喻》一章系鲜卑语,根据蒙古语可考其意为“军歌”“战歌”“武歌”。?《乐府诗集》收录的《企喻歌辞四曲》显示,《企喻》指代武夫马上之歌,包含多人唱和部分,内容多涉及军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