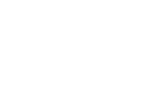木镇的屋檐

我居住的木镇,所有房子的烟囱都朝上,所有的屋檐都向下,屋檐下鸟巢里的鸟雀头都朝外。是的,在冬季,最避风寒的就是在黄昏时回家找一个栖身的屋檐。早先木镇的人去世了,坟墓里脚都对着村口的方向,好像翘向屋檐,伸到屋里去。
每次从外面回来,我都感到木镇的局促与狭小,连挂在白杨树梢的月亮也只有一半,瘦瘦的,清癯,好像另一半被城里夺去了。我真的觉得木镇很小,如废弃的卷角起毛的邮票,有时又真的觉得它是那样的敏感,如一个刺猬在平原的深处,一有响动,就胆怯地蜷缩起来。
人对故土时时反顾。有时又觉得,无论你离开土地多久,从乡间走出多远,总能感到隐隐有一根脐带连着你和乡村,这脐带如输液管一样,给你带来营养。
在外地,我常会无端想到——夜里,窗外有风,父亲常在风里早起。那时,风吹动窗棂上的纸,噗噗响,父亲拿着扫帚走出篱笆门,把落叶和枯枝弄到一起,然后背到灶下。到了晚间,灶头的火照红了母亲,而墙上筷笼里的筷子,也成了红的,一根根如铅笔。在灶下,母亲在柴火的灰烬里埋下一块红薯,到了夜半,在睡梦里,你接到烤得焦焦的红薯,觉得乡村的柴草和炭火烤出的红薯,那才叫烤红薯——这不是手艺,是乡下母亲们天生的独门绝技。这里面有母亲的体温,有父亲收拢的枯枝落叶,更有大风把漫天的星星吹落后,父亲走在风里的踉跄。
确实是狭小局促的木镇,每当夜里风起之时,我总有一种担心,无尽的落叶,会把那像草绳、羊肠一样的小路淹没吗?或者路也会被风吹断,一截被风吹到另一个村子吗?
我在城市无端地失眠,被那些夜里肆无忌惮的光弄得心惊肉跳。

登录后获取阅读权限
去登录
本文刊登于《读者》2023年1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