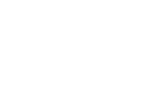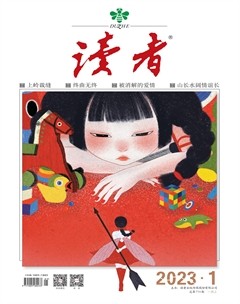我留学时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小镇四周被玉米地包围着,商场里也没有太多好一点儿的品牌。
时日一久,留学生们也养成了自嘲精神,戏称这里是“村儿”。在高速公路上开两个小时车去一趟芝加哥,叫“进城”。在品牌店扫一通货,去唐人街吃一顿重庆火锅,将买的东西开车拉回来,一路夕阳相伴,玉米地绵延无边,便是“回村儿”了。
解馋、扫货之类的事可以进城解决,但理发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女生还好,往长留就是了。可男生就不好办了——更准确地说,是家里条件没那么好的男生不好办。
韩国大姐李金姝的理发店,刚好方便了陈焕生这样每月剪一次、每次最多消费二十美元的男留学生,所以很受欢迎。
李大姐的店在镇中心的主街,门脸小。当街挂个牌子,再穿上一对风铃,朝九晚五迎风叮当作响。下午五点一到,她就收了风铃,牌子哑了,便是收工了。留学生们虽频繁光顾她的店,都说那风铃声好听,暗地里却笑她的英语太差。
李大姐的店前后有四位理发师:康德姐、纳沙、迭戈和老板李金姝。先说这康德姐:只要她出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肯定排她的号,一者大家同是中国人,二者小费不用给那么多。
据说,康德姐在北京也拿过博士学位,可惜专业太形而上,搞的是什么存在主义,若非在五道口淘香烟时认识了一名美国人,漂洋过海嫁过来,她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村儿里呢?
她嫁过来后生了一个女儿,女儿是地地道道的混血儿,脸上那漂亮劲儿就像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可惜她丈夫出了车祸。那是一个细雨天,她丈夫在高速公路上开得飞快,为了躲一头站在路中间不知所措的鹿,车和人在空中翻了两圈。她丈夫生前是这里大学的助理教授,跟许多三十出头的美国人一样,处于偿还各种债务的爬坡阶段。康德姐这边绿卡还没办下来,英语讲得也没那么利索,一夜间就成了遗孀——还是偿还各种债务的遗孀。
正是从这时起,康德姐抛弃了那一书柜的萨特和加缪的著作。她抱着女儿,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黑白黄肤色的兄弟姐妹分享她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