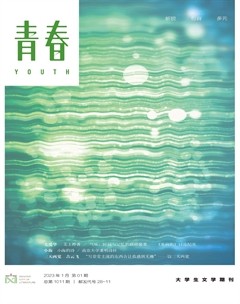“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美德即知识”,庄严的灰白色塑像,鱼形眼睛中却为何总是缺少眼球?这样的问题显然无须关心,嚼碎句子再通通咽下即可。浪漫主义,这是个令人心生向往的词汇,但焊在课本上,一切浪漫或许都要被削掉大半。往下,再往下,下一个单元……横向排列的文字开始四处游走,严整的秩序随即被打破。猛然灌下几口咖啡,又狠狠掐住自己的胳膊,书页上的内容这才开始重新规整起来。
清嗓子的声音由站在讲台上的班主任发出,没有人抬头。那些关乎前途的长篇大论早已无数次侵入我们的血液,诱发了抗体。黑板边上灼人的倒计时数字总是在无情锐减,根本无须谁来多言。突然,有个陌生的声音传过来,爵士乐似的,能够叫人心甘情愿返归现实世界。爽利地说了些什么,还未听清便已然结束,台下响起机械又无力的掌声。
烟草味的风刮到身边的座位上,定下来。那个悦耳的声音对我说:“你好,我叫李遥迦,你叫什么?”我觉察到她正在打量我,出于极为自然的好奇心。“陈韵。”我低声回答了句,抬起头向她看去,一眼便愣在那里:我从未见过如此鲜明的人物,浑身上下充满了叛逆的可能,眼中泛着雀跃的光,在这一屋子的温暾沉默中显得格外出挑。
她默念着我的名字,同时从自己的背包里翻出了盒巧克力,轻轻放到我的腿上。我刚要开口拒绝,她便隐秘地指了下讲台上的班主任,又做出“噓”的手势,之后便像个没事人一样整理自己的东西。我明白她是好意,也正是这番好意让我受宠若惊。我的头发短至耳根,校服早已被洗到发白,袖口处还有缝补过的痕迹。一副身体陈旧而又破败,运作时便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不合时宜的焦油味黑烟反复升起……我不知如何是好地看她一眼,她便偷笑起来。
“十五分钟,默写文言文。”移开目光,接住前排传过来的默写纸。一晃神,手指被那白而脆的薄片削出个口子,血渗出来。怕蹭脏写字的地方,拿卫生纸胡乱擦了两下,之后便以那心无杂念的惯有姿态埋头苦写起来。她并不参与,只是自顾自地把手机塞进抽屉,纤细的手指在聊天框间翻飞。
一天之中,我们仅有的交集围绕着复习资料展开。做过的卷子发下来,她是没有的,我便邀她合看,她也欣然答应,还极力做出专注的样子,小口吞咽那些牢靠的符号。我总觉得自己成了狱监,非要用一堆破纸将她铐在这里。讲台上的声音说“来,我们现在订正一下答案”,鲜红的权威便骤然填满栅栏。
终究还是难以忍受下去。她顺手抄起支笔,凤蝶便飞过来,一双翅膀扇动着,静默地落在试卷边缘,草木将在其身下蔓延。这一点生机,在满目疮痍中肆意高歌起来了,然而却突然间停住。她想起这并非自己的领地,于是在抱歉地微笑后将卷子推向我这边。我很想对她道谢,却总觉得有些古怪,最终还是把话咽在了肚子里。
时间是稀薄的。在这间屋子里,所有人都拼命地吮吸着、挤压着。与成绩无关的一切都只能是身边的一瞬,没人拥有为其停留的资格。于是,仍然像往常一样,头扎下去、埋下去,固定在那儿,经久不变地行着大礼。困倦时便站起来,试图通过新一轮的僵硬让全身变得柔软,又很像是在忍受酷刑。她则有着属于自己的空间,总是置身事外。偶尔抬起头扫一眼四周,才会与这团庞大的笃定产生暂时性联系。我们坐在一起,却过着两副时间。
那天晚自习后,我从车棚里把车子推出来,一路吱呀到校门口,正看见她跃上一辆黑色轿车。轿车里应该有空调,有空调就会很暖和。在大风戳穿旧棉服的时候,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路越骑越黑,越骑越泥泞。摊贩们把污水统统泼到路边的井盖上,仿佛那小小的洞口有着容天纳地的能力。水边流边凝,混着泥土结成脏冰,日夜散发着腥臭的气味。
家里,母亲在等我吃饭。一大锅馄饨摆在桌子中间,腾腾地冒着热气。我洗了手,盛上一碗,吸溜吸溜地吃着。母亲也吃,边吃边问我:“考得怎么样啊?”我说:“年级第五,数学考砸了。”母亲用不锈钢大勺把几个馄饨续进我的碗里,笑脸在勺子上闪来闪去。“找张老师补补数学吧,给你打好招呼了。”桌面上有条裂缝,里面滋生着污渍。我直直盯着它,想要盯出个所以然来。“钱的事儿不用担心,我和你爸都支持,好好学就行了。”父亲在外面跑车,已经一个星期没回家了。
家,家?我的家,她的家。所以,她的家该是什么样的呢?万分疲惫地躺在床上,人却睡不着。她家一定是干净的、柔软的,空气中大概还会飘着茉莉花的甜香。阳光见了那乳白色的窗帘,都该只舍得轻触,重一点都不肯的。风吹过,那缕柔顺便随之飘浮起来。还会有一只猫,大抵是波斯猫吧,整日趴在温厚的沙发上睡觉,醒来时便三步并作两步跳到她的怀中,用那双异色的眸子看她。这样的时候,她便笑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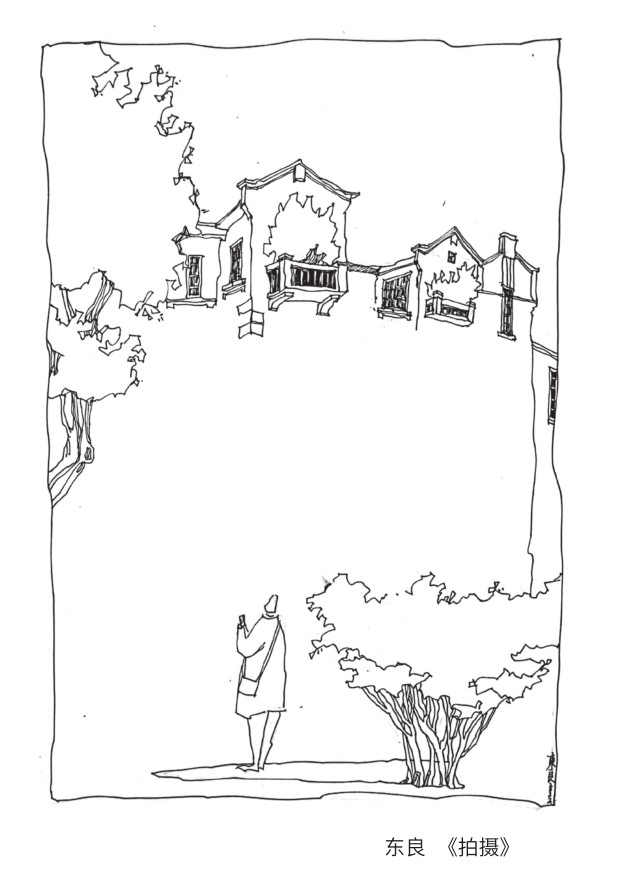
不过,直到很久以后,我都未能印证有关她家的猜想。她身上的流言实在太重,压得我不敢往前半步。不到十八岁的男男女女们将一抹又一抹残酷的字眼打在她身上,直至将其涂抹为一个妖魔。但依我所见,她只是每日化妆,身上偶尔带点酒气,隔三岔五就翘掉晚自习,但说到底也不算什么大的罪过。更何况,她爱笑,笑时眼睛便成了雨后的水洼,叫你生生跌进去。她一边笑,一边抄我的作业,递给我零食,拉我去操场透气……
粉笔是惨白色的,黑板是墨绿色的,卷子和书都是灰白色,油墨则呈现出浓重的黑。然而,无论是怎样的书写工具与载体,平行线就是平行线。立体几何大题多会带着股“放你一马”的温和,可终究还是规整。线连错一条,数代错一位,很遗憾,满盘皆输。因此,我无法与她接近。接近,便意味着混乱;混乱,则意味着背叛。也不知是怯懦滋生出恐惧,还是恐惧孕育了怯懦。总而言之,我对自己说:“马上就要高考了,如果不努力,就没有办法考上理想的大学,你这一辈子就毁了。”用干瘪的话语自我催眠,用干瘪的话语来人为划定界限。
然而,在她低着头回到座位上开始大哭的那一刻,我便下意识地抛弃了所有荒诞与可悲,以及那些固执的距离。四周嘈杂一片,她被安置在棱角分明的玻璃柜子里,有些人好奇地看着,像是在看一团瘟疫。那些哭声冲出去,又被撞回到她的身体上,碎裂得十分彻底。没有人应当这样难过,何况是她。轻拍着她的后背,她抖个不停。“那是我姥姥留给我的……保佑我的……”她说。我说:“好,不要哭了,等着我。”白炽灯下,那些眼泪呈现出敏感又脆弱的姿态。
“老师,请您把李遥迦的挂坠还给她。”我立在办公桌前,班主任依旧在判卷。或许我该解释,最不济也要添些软和的修辞,抑或是根本就不该来。笔尖划过卷子发出轻微碎裂的声响,我的头有些发烫。又将话说了一遍,眼看着自己的声音聚集、上升,在敦实房顶的依托下游了两圈,便散尽了。
班主任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极为怪异的和蔼,似乎是捍卫了我的什么,又想要我以什么作为报答:“戴首饰违反校规校纪,本来不应该现在就给她的,但既然你都来求情,那就先拿回去吧,让她别再戴了。”佛形的坠子,握在手里是温润的凉意,随时都要滑落似的。我说“谢谢老师”,然后意欲离去。“对了。”我的心紧了一下,将身子转回,“昨天那篇作文得分不高,回去可得好好改啊。”“好的老师。”我这样回应道。
我将坠子给了她,她便拥有了失而复得的欢喜心情。各式各样的答谢过于浓重,像是她为我买来、哄我喝下的那杯果茶:满嘴黏腻的甜。我也就顺势用加工饮料的方式调配我们的关系。白开水兑进去,味道便淡下来,味蕾连带着心一同乏味。所谓的理智驾驭着属于我的一切,监督着我的一举一动,由梦呓到呼吸,日子也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冬天渐远,转眼已是春天。各种试卷和复习资料从天而降,源源不断,堆积成山。我数学底子太差,此时便也顾不上其他,只是一味地听讲、做题,恨不得把命交出去半条好换取零星分数。母亲则开始每日为我熬鱼汤,乳白色的,泛着咸腥的气味。喝的次数多了,便有些想呕。前路雾蒙蒙一片,也是鱼汤般的白。我是父母的好孩子、同学们的好榜样,即便身体中的某个部分只想尖叫着烧掉所有的试题、摔碎腥气的砂锅、径直倒头大睡。
一点钟到五点半,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倒头大睡是可以实现的,但梦却做不长。满操场的人,同样的姿势,同样的颜色,静默地等。台上的校长声音洪亮地说:“祝大家高考顺利!”台下的人听罷便卖力拍起巴掌,似乎是想用声浪把那话托到天上去,让神仙也好好听一听,以此达到祈福的目的。台上的学生高昂地喊:“拼搏一百天,拼搏,拼搏,拼搏!”台下的人听罢便亢奋地跟上,响动直冲我的耳道,猛烈地撞击大脑。继而,充斥着上进因子的音乐猛然罩下来,我们就这样盖上“生产合格”的大印。
却还是搞砸了。装作呼吸平稳的样子,装作胸有成竹的样子,走进去,坐下来。录音机中有女声传出,这声音大概也是衡水体吧,不然怎么会规整得要命。拿到试卷,填写基本信息:陈——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