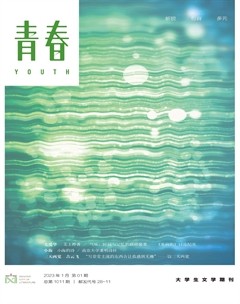1
我时常分不清是我梦见了记忆深处的故乡,还是故乡把我拉进它庞杂的梦境中。
有时我奔跑在田埂上,视野里翻滚着绿麦子、黄麦子的浪潮,祖母在不远处漂浮着绿油油水草的小溪旁捣衣。“啪——”七零八碎的捣衣声穿透薄薄的夜幕,洒向溪水,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丘,沿着蜿蜒的小路潺潺流去,漫浸在沉静如水的夜色苍茫中。有时在下雨,我与祖父同坐在屋檐下,他闭着眼睛假寐,身后的竹椅在风中咿呀作响。雨沿着屋檐的凹槽处滑落,打在泛着白光的青石板上,清脆的凉意便入了耳朵。日子一如既往地久长。
上学之前,我的童年是与祖父母在乡下度过的。那是个江西西北部的边远山村,幕阜山自西南向东北绵延到这里。在江西境内,与幕阜山隔岸相望的另一条山脉,名为九岭。一道九岭,又将九江与南昌分隔开来。九江的北面,修江从山垭处跌落,蜿蜒穿过幕阜山与九岭相隔的腹地,带出了一片生机,因此得名为“修水”。沿着修江的支流远远而去,岸边零星散布着各个村庄,我的家便在其中一个小小的村庄里。一片望得见尽头的田野,三面圍着连绵的幕阜与九岭山脉,有如屏障。村里疏疏落落住着几十户人家,皆是剥落了泥墙的土坯房,它们背后倚靠着连绵青山。重重青山围着房屋,斜仄的房屋和树木散落在小路旁,与小路相连的,是从各处通向田野的田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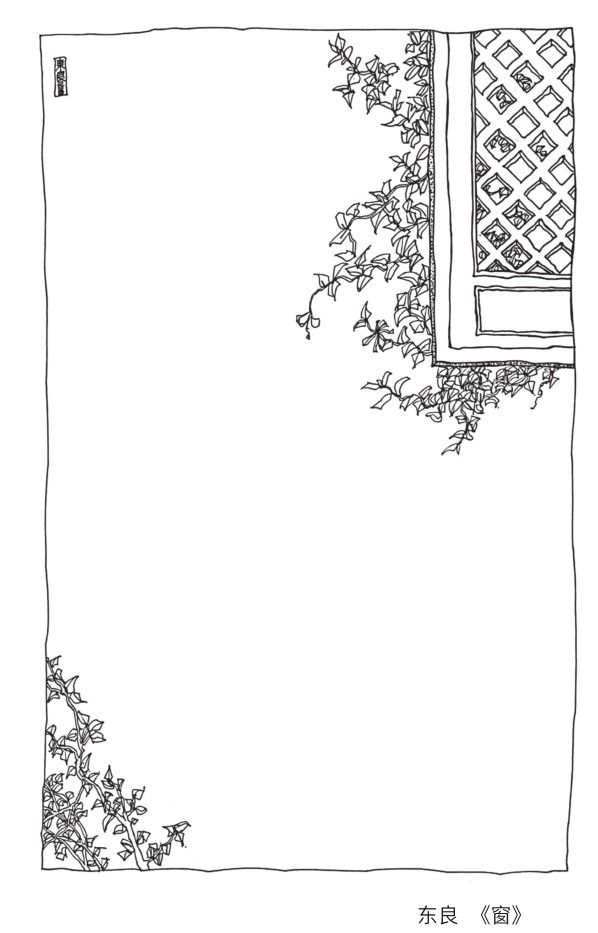
家门口不过几十步的距离,有一条浅浅的小溪,两岸的树枝垂落到溪水里,在阳光下浮漾出细细密密的波光。祖母因害怕我调皮捣乱掉进溪水里去,很少将我带到小溪边。偶有一两回,于我而言,便是宛如天赐。祖母将花花绿绿的衣裳从哐当作响的铁桶里倒出来,不顾厚重的青苔和黄泥,把浸了水的衣物重重拍在壁边,她甩甩手,袖口往腕上卷几圈,一手扯住要往水里去的衣服,一手拿起小木棒在衣服上结结实实地敲打。我坐在一旁打量溪水里的影子,一条鱼,一片树叶,几块灰白的云团,还有在涟漪里浮动的捣衣身影。亲缘血脉在这些没有生命的衣物中流动,穿在身上,又是厚重的温暖。
有风吹过来,两旁的芦苇就在风中微微摆动,不远处田野上新翻的泥土香味,随着风一阵阵飘过来。我再也坐不住了,转身朝田野跑去,与伙伴们一同疯玩,总是忘记日暮迟迟,两位老人还在等我回家。日头西斜时,祖父总从门口的树上摘下一根长满荆棘的“刺棒”,呼喊我的名字。天色渐渐黯淡下来,祖父的喊声也更加急促,他的嗓音在时间的淬炼中愈发淳厚、高昂,回荡在村庄里,远远的,像一支古老的歌谣。
时间就这样在祖父、祖母无数次的等待中偷偷流逝。上学前一天,父亲将我从乡下接到城里。他把我抱上老式自行车的后座,那是一块粗糙的小木板,我们沿着黄泥小路离开。我扭着脖子向后张望,祖父、祖母站小路中央,慢慢地、慢慢地,他们像旁边的树、屋子一般静默无声。我见过许多东西在风中伫立,都没有他们那么像岿然不动的雕像。自行车在风中缓缓地走,金属链条摩擦出细微的声响,我在自行车的后座,看着他们被黛色的山脉、昏黄的灯火晕染成相似的颜色,直到完全与故乡融为一体,隐没在茫茫夜色中。
我已经沿着小路远去。
2
彼时的我,没有想过,后来我竟再没有真正地回过故乡了。
二〇一二年夏,祖父过世了,祖母也不在老房子里住了。祖父的离去似乎带走了她对于家的归属感,一种叫空虚的东西正在酝酿,弥散在她寂寞的晚年。很多次,我看见她呆坐在城市的落地窗前,浑浊的目光投向不远处的山峦,许多尘埃在阳光下飘浮,最后跌落到她的视线之外。又或者,她的视线早已越过山丘,落到她魂牵梦萦的老屋。老屋坐落在幕阜山与田野的间隙里,是只有三间屋子的土坯房。正面三个洞里,一左一右塞着木制窗框,常年糊着泛黄的报纸,中间是简陋的木门。从门口踏上几个歪歪扭扭的台阶,便是有天井的院子,从这里可以窥见一块长方形的天空。院子后头,几块结实的长木板潦草搭成茅房,一墙之隔,圈养着大大小小的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