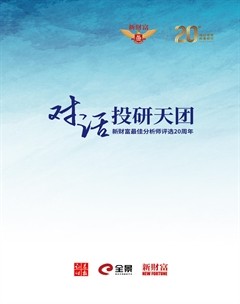国内外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研究需要与时俱进
新财富:债券投资者对宏观基本面会更为重视,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概括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需求的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2022年的会议指出三重压力仍然较大。您如何研判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形势?
张继强:这几年,宏观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地缘环境发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首要任务;全球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在变化,过去更多地讲效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多地讲公平,安全和公平成了重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研判框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思维方式上,过去是成长的角度理解很多问题,现在很多时候是以结构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而且,以前我们的聚焦点在于需求端,比如三驾马车等,现在往往看的是供给端,比如2022年全球通胀,是供给因素所导致的,而不是需求。
2021年中央提出了“三重压力”,正是过渡期特有的一个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供给、需求和预期的层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自己也在适应这种新的环境,这可能是疫情之后的一种特殊现象。也许经济的潜在中枢在逐步放缓,而且,房地产行业再也回不到过去,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经济结构可能会更加健康,产业会继续升级。
新财富:放眼全球,您怎么看待通胀产生的原因?
张继强:这波通胀的原因比较复杂,跟以往的机理不太一样。我们以前提到过,全球有诸多滞胀基因。第一,是逆全球化。以前全球贸易的基础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但是现在会依附于安全,甚至价值观、公平,安全冗余会牺牲效率、抬高成本。
第二,是新能源,包括绿色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有利于人类的持续发展,但客观上也会抬高能源的成本。过去几年,矿业巨头、油企,被欧美养老金大量持有,这些股东的诉求是稳定的分红,就不鼓励企业做capex(资本性支出),导致市场没有新的供给,一旦需求起来,能源价格就容易突然上涨。
第三,中国供给侧改革、老龄化等也改变了全球的供求关系。
所以,今天看到的情况是,全球这一波通胀超乎大家的想象。2021年,美联储说通胀是一个短期现象,2022年已经不再提了。
单纯从美国的通胀来讲也很有意思,它有供给、需求、货币政策三重原因。
第一,供给方面,有俄乌冲突的因素,有过去几年传统行业资本开支减少的原因,所以,一旦需求起来,弹性就特别明显。当然,这跟劳动力的供给也有关。疫情之后,很多劳动力不愿意出来工作了,加上美国收紧移民政策,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减少,也从供给端推升了通胀和工资,而且,低收入人群工资涨得比高收入人群要快。
第二,需求方面,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疫情期间扩张了将近一倍。这是什么概念?大量的资金通过MMT直接发到老百姓的手中,以前的QE沒有发给老百姓,更多在金融市场推升资产价格。它比当年伯南克说的“直升机撒钱”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还要更直接,影响更大。这造成一个结果的原因,就是整个需求突然膨胀起来了,供给又跟不上,当然价格就有了剧烈的上涨。所以,这一波通胀跟欧美大肆放水或者货币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货币政策滞后。2021年,通胀其实就有苗头,从正常的周期来讲,美联储就应该干预。但是,美联储认为这是临时现象,还是把就业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觉得就业数据不好,加息要等一等。结果到2022年发现,就业突然变得非常火爆,但是,通胀已经有点失控的风险。这个时候急匆匆地加息,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紊乱。
新财富:您觉得货币政策的框架会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怎么判断货币政策所处阶段?
张继强:货币政策是与时俱进的。上世纪70年代全球出现一轮滞胀,美联储主席沃克尔采取的方式就是坚决地通过加息打击通胀,维护了央行权威。从那之后,全球形成了一个思维:控制住通胀是央行唯一的目标。所以,当时非常流行单一目标制。
到2008年次贷危机前夕,一个新的现象在全球出现:金融泡沫起来了,但从通胀层面看不出来,因为资金可以进入实体经济,也可以进入虚拟经济体系,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危机。
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央行也有很多反思:单一目标是不行的,要与时俱进。例如,中国实行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即一方面是传统的货币政策,盯住经济周期;另一方面是用宏观审慎政策,盯着金融周期。
往后推演,我觉得还有一些新的现象值得关注。比如,货币和财政之间更紧密的结合,这几年已经出现了,包括美国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等。在中国,大家对此也有很多讨论但方式不同,比如政策性金融等。
当然,这两年,央行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提出“内我为主”兼顾内外平衡,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加大技改再贷款等结构性政策力度,推动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上下波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零利率、供给逻辑时代,利率资产轮动敏感性降低
新财富:如何概括利率周期的轮动对于资产配置的作用?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张继强:过去的周期研究中,最典型的模型就是美林时钟,它描述的是从增长、通胀到资产的表现。但是,增长和通胀是央行关注的两大目标,也是影响利率的两大指标。换句话说,美林时钟其实描述了一个从利率到资产价格轮动的关系。但我个人觉得,这种框架在过去几年遇到的挑战比较大。
正常时期,利率低一点,企业有利可图,就会开始生产,然后就扩大了需求。经济过热的时候,稍微提高利率,压抑需求,企业发现无利可图了,就会停止生产,经济慢慢冷下来,需求就弱化了。
但是现在,一旦进入零利率时代,正常货币政策失效,欧美等国推出了QE操作,这个阶段,资产的表现跟正常的利率调节的逻辑完全不同。最典型的例子是,黄金可能变成一个货币的替代品,表现很好;但其他资产,尤其是股、债,有可能同涨。零利率意味着流动性很充裕,就会推动所有的资产价格上涨,从利率到资产价格之间的轮动关系就被打乱了。
此外,这个逻辑其实还是需求端的逻辑,是从利率到需求端,但是我们发现,最近几年影响市场的不仅仅有需求逻辑,还有供给逻辑。比如,为什么2022年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能涨那么多?是因为过去几年传统行业的capex比较少,叠加了俄乌冲突对供给冲击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重视需求的同时,还要重视供给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