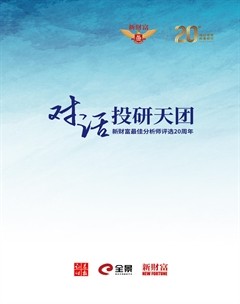观测未来经济增长三指标:储蓄率、工程师红利、市场化
新财富:国内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40年,未来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郭磊: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可能一些驱动因素在慢慢减速,但同时还是有一些因素能够支撑经济中长期偏高速增长的。
我比较关注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储蓄率明显偏高,国民储蓄率这两年在45%左右,而全球大约在27%、28%的样子,发达国家会更低,在23%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具有发达经济体一倍的国民储蓄率。从经济学的逻辑上看,储蓄率可以带动投资率,投资率带动趋势增长率。
第二,工程师红利,这包含过去30年我们在教育、科研、应用端研发上的积累。国内科研人员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国内企业PCT(专利合作协定)专利的申请量等,都展示中国目前处在工程师红利的释放期。它们所对应的创新动力是未来5-10年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动能。
第三,中国经济目前依然有比较明显的市场化空间。如果未来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推动统一大市场,逻辑上可以带动全要素回报率的进一步提升,这是从中长期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偏高增长的另一要素。
新财富:当前强调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化,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的精髓?
郭磊:我理解的高质量发展包括几方面。第一,有相对平稳的速度,即经济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增长轨道上。第二,结构上实现优化。比如消费、投资、出口等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逐步优化,上下游的产业链逐步优化,经济和非经济过程比如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步优化。第三,产业进一步升级。这一过程中,高附加值、技术型、高科技类的产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此外,全社会更广泛的群体,可以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回报。如果能同时做到这几点,就是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新财富:2017年,您提出“朱格拉周期”和“工程师红利”的研究框架。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疫情防控,站在当前时点,这两个研究框架还有效吗?如何借此来观察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郭磊:以5000家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来看,2008年之后这个指标就经历了一轮上行,2011年以后进入下行周期,2016年再度触底,也就是说,2008-2016年算是一轮朱格拉周期。2016年之后,经济活跃度上升,制造业投资有逐步回升的趋势,这是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特征,但同时,政策继续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包括2017年之后的金融去杠杆、实体部门债务化解,以及产业基础升级等,对朱格拉周期的形态有影响。目前制造业的投资高增长一是表现在新经济领域,特别是一些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复合增速非常高;二是在传统制造业的部门的技术改造投资,方向是低碳化和数字化,这也是这一轮朱格拉周期的主要特征之一。
工程师红利是中国未来10-20年的人口红利。上一个10年,我们在人口数量优势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外需型的产业链,人口红利背景下制造业有成本优势,但是随着人口增速逐渐放缓,人口数量优势在逐渐弱化,同时制造业也已经度过了初级阶段,工程师红利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高研发密度、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推动制造业升级。所以,未来10-20年,工程师红利依然是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带动力量。对这一点我相对偏乐观。
后疫情时代,宏观经济政策要有新抓手
新财富: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中国的经济特征概括为三重压力,2022年的政策在稳增长方面发力,2023年政策也是稳字当头。您怎么判断后疫情时代,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
郭磊:外需在2020年、2021年一度比较强,部分与商品对服务的替代有关,这对应着海外主要经济体补库存和中国出口的超高速增长。但是现在看海外经济,美国的制造业周期已经触顶回落,需求的逐步放缓会通过其进口需求映射到我们的出口上,所以,出口没有办法继续加速。扩内需的必要性凸显。
在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经济存在一定的环比修复空间。但同时,在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消费和服务业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天花板效应。因为在这个阶段,居民生活半径缩短,社交距离上升,而且有一些消费形态可能会消失,或者至少在量上受损。可以观察到,过去的几个季度里面,消费的增速跟2020年之前有明显的差距,这就带来总需求的缺口。
后疫情时代,针对总需求缺口的稳增长是必须的。从增长结构来看,消费环境要逐步修复,消费是内需的基础。除此之外,可以用固定资产投资去适度填补消费缺口。实际上,202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体现了这样的思路,比如留抵退税,是为了带动制造业投资;财政前置,是为了带动基建和新基建投资;因城施策,是为了带动地产投资。在消费恢复正常之前,固定资产投资要保持扩张来弥补总需求。
新财富:如何看投资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估计未来投资增速能有多少,靠哪些力量可以带动投资?
郭磊: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从2035年远景目标“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倒推,未来15年,中国经济年均复合增长率要在4.7%左右。考慮到长周期经济增速逐步下台阶,第一个五年增长5.3%、第二个五年增长4.8%、第三个五年增长4.2%算是中性假设。
从这样一个目标倒推,固定资产投资同样存在下限。比如GDP要达到5%以上的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就不能低于5%,否则按消费、投资、净出口计算,整个式子就打不平。倒推一下,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需要在6%-7%,基建也不能低于5%-6%,地产不宜低于零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