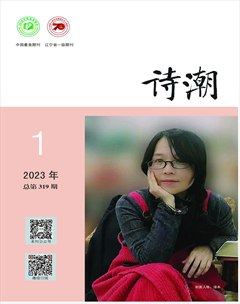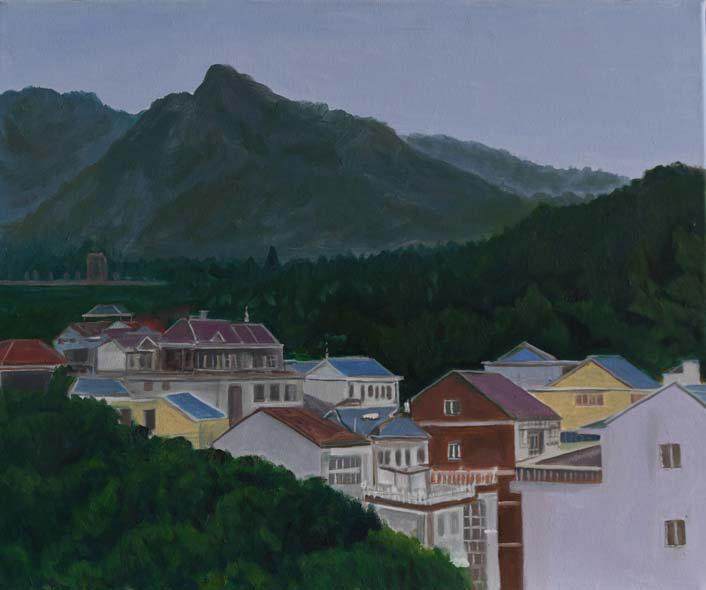
我见过许多诗人。大多数时候,在遇见诗人之前,我就已经阅读了他们的诗歌。相遇时不曾读过的,也会通过手机搜索了找来读。总之,在与诗人们相交之前,我就已经对其诗其人有了一个初步的个人判断,而后才真正认识了诗人。他们有的人如其诗,有的则和诗歌构成极大的反差,如此知其人,论其诗,又多了此前不曾有的一层领悟。
而我与诗人沉河的相遇,则全然不同于以上情况。第一次见到沉河,是在一个冬日举行的诗歌研讨会上。房间里是你来我往的学术讨论,沉河和我站在门外,娓娓说起多年来从事诗歌出版的心得。不久之后,我又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沉河的办公室——长江诗歌出版中心,据说是全中国最具诗意的办公室,室内摆满了葳蕤蓬勃的绿植,绿萝和幸福树的叶子几乎要攀上天花板,诗集多得一整墙的大书柜也装不下,随性堆放在植物的间隙,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石头和茶壶。沉河就在植物和诗集的簇拥里编诗集、抄经、喝茶。数次见面,我认识的沉河即是一个现代隐士般的文人,一个生活即是诗的人。与此同时,我也开始阅读沉河的诗歌、散文,随着交流和阅读的深入,我逐渐清晰地意识到:如果说对于其他诗人,他们的个人生活参与构建了我对他们的诗歌印象,诗人成为诗歌的注脚;而对于沉河,情况则恰好相反,我关于沉河诗歌的全部阅读,只是印证了我心目中名为沉河的诗人的形象,在他这里,诗歌成为诗人的注脚,或者更为准确地说,诗歌成为某种生命范式的明证。
沉河的诗绝少叙事,日常生活无法激发他的兴趣;他的诗也不常描写,他并不关注那些内容和形式皆已确定的部分。他操持的是说理与抒情相融汇的笔墨,他的许多诗歌带有哲学思辨的意味,尤其他早期的作品,那种抽象的、辩证的思维随处可见,然而他的诗歌并不是枯涩的哲理诗,而是带着抒情的厚度与温度。在他的写作中,有一类诗歌尤其引人注目:写作时间跨度长,由碎片化的短章构成的组诗。从早期的《伤春》《河边公园》,到《随手集》《你我集》,再到近期的《五十一岁记》《五十二岁记》《无论》,尤其在《无论》里,这一写作偏好达至巅峰。《无论》的写作,始于2015年,终于2021年,全诗共分为7个小辑,每一小辑又有24节,暗合二十四节气,这些诗歌每节大多四五行,以最坦率的方式记录了一个诗人内心世界的变化。另一组诗《种植诗》由8首诗组成,这8首诗其实都可以单独成篇,但诗人更愿意将之统摄于同一主题下,成为一首连贯的、互文性的“大诗歌”。这些时间跨度大、主题也不集中的诗歌碎片,共同构成了诗人书写同一主题的完整拼图,是诗人理想中的世界向现实生活所投下的星辰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