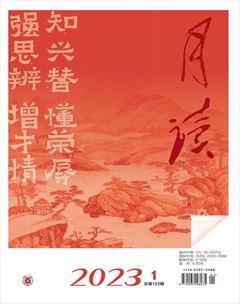“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毛泽东的诗词成就,首先得益于他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毛泽东学诗、读诗,从少年到晚年,终生不辍,累积而成中国古典诗词渊博学识底蕴。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并非出身书香门第,谈不上“家学”基础。他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接触,始于童蒙时期的六年私塾生活。私塾启蒙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都是韵文诗歌。继而读“四书”“五经”,其中就包括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少年毛泽东天资聪慧,这些诗文,他都能背诵如流,还能默写出来,学习上不需要塾师劳神费力,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
在古典诗词造诣方面,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是最后一位塾师毛麓钟。毛麓钟自幼在祖父的熏陶下,专心潜攻诗书,学绩超群。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10年)春,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钟家里读书。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读一些时论和新书。”在东茅塘私塾读书时的毛泽东,经过两年多辍学劳动的磨炼,有感于乡间生活的贫乏和读书求知的不易,因而在就学机会失而复得之后,学习开始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由天资聪慧转向天分加勤奋。毛麓钟也抱定一个心愿:精心教育培养毛泽东,用全部的知识与智慧去雕琢这块“璞石”,使之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毛麓钟让毛泽东背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他觉得诗句虽短,内容却情深意长。毛麓钟很喜爱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认为它反映了古人珍视友情的思想主题,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事,毫无雕琢之工,读起来琅琅上口,很适合青少年学习模仿。他将这首长诗亲手抄录给毛泽东,让其吟咏、揣摩。
由于毛麓钟的严格训练,毛泽东进步很快。他熟读了几百首古诗,即便是很生僻的诗句,竟也稔熟于心,倒背如流。从南宋“将军诗人”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到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再到庾信的“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消亡?桐何为而半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都能即兴吟唱,信口背诵,毫无差池。
毛泽东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随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他在一师求学时有多种手迹留存。“马日事变”后为防反动派迫害,他的族人们将他存放韶山家中的书籍信札笔记等物搬至后山烧毁,他的堂兄、塾师毛宇居冒险抢出并保存了一小部分,只有47頁,94面。笔记用的是直书九行纸本,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是听课笔记,也包括一些读书札记,现已被收录在《毛泽东早期文稿》当中。毛泽东手抄的《离骚》和《九歌》手迹,是毛泽东早年认真研读中国古典诗词的直接佐证,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过多少古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离休干部张贻玖,1982年曾由中宣部借调到中南海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