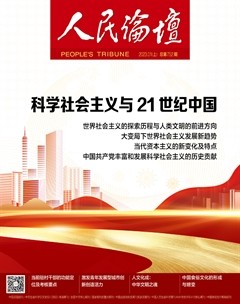【关键词】“选择恐惧症” 退出可能性 家庭主义 分配制度改革 多元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选择恐惧症”近年来成为青年群体中的自评热词。许多青年倾诉自己时常陷入选择困难症泥潭,越是反复权衡利弊越是不知道最终如何选择。每一代青年都有每一代的“选择”,而当代青年群体拥有相比于过去青年更丰富的物质资料、更多样的就业道路,却也更加不知、不敢做出人生中适合自身的各种选择,特别是一些学历较高的青年甚至出现了“逃避就业式考研”以至“逃避就业式读博”等新现象。理性做出选择是青年群体成长成才、勇于承担选择后果的重要一课。对于年轻人职业或学业方面所出现的“选择恐惧症”以至于进退失据的严重后果,需探究其深层原因,探讨当代中国青年群体如何看待选择与承担责任,从而根据自身特长与条件进行理性选择。
从传统的“个体低选择”到当下的“选择恐惧症”
严格意义而言,个体的“选择权”是当代个体主义权利观念与行为被逐步承认的结果。传统社会之中,个体诸多事务是由家长来做决定而并不存在个体的“选择权”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对于士农工商的职业选择,子承父职是农业为主的社会就业形态的必然结果,即使是学工或经商可能突破了家庭父子兄弟关系的局限性,师徒关系之中也倾向于师父有权介入乃至决定徒弟的很多事务,以至于在价值层面确立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准家庭主义伦理定位。即便是读书考科举而获得任官资格,除了可能的家学传统的文化资本,普通家庭能否提供较好的经济基础给小孩读书常常也是由较为富裕的家长来做决定,因为这涉及是否需要进行长远的文化资本投资。要言之,个体的职业选择权一度是操之于家长的,而婚姻自主权则更加是由家长或准家长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来进行选择的。父权式家庭主义的家长决定而不是自我选择,是传统社会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与家庭生活方面的基本特征。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在单位制与人民公社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下,单位领导与师傅常常是决定个人命运的主宰,个人处于在职状态下的升学、调动以及结婚离婚的选择都需要经过单位的审批。单位制在提供保障与福利的同时,一度压缩了个体在教育、工作及私人生活中的选择权。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个体在各方面的选择权无疑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各种社会政策随时调整的多变性,个体至少在求学与就业过程中的偶然性机遇是更多的,这也就使得诸多升学与所谓职业选择本身也是一种“缘分”。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不少年轻人奋斗与发展的诸多偶然性或许并不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考已经基本规范化与可预期了,虽然学校专业选择、是否继续深造及最终职业选择仍然有相当的偶然性,但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在其中的能动选择性明显增强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或许曾经是个体自主选择读书深造还是就业工作的黄金时代。
然则,对于“90后”“00后”的当代青年而言,“选择恐惧症”却正在成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从高考的专业选择开始,当下高中生对一些大学学科分布可能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种信息的相对完备性反而使他们产生了专业报考中的焦虑,核心的问题可能还是对于未来的就业前景的评估与选择。学生感兴趣的专业如果就业前景并不好,选择往往相当艰难,甚至可能与家长之间就专业选择产生比较激烈的矛盾。与此同时,为了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暂时逃避就业压力,当前研究生报考人数也不断增加,2017年全国考研报考人数还仅为201万,2021年已经增加到377万人,2022年快速上升到457万人,2023年更进一步达到474万,再创历史新高。如果说读研可能还是一项有利于就业的理性选择,那么读博与否的“选择恐惧症”则更为明显,一些学生读博已然不是出于对科研的兴趣,而是可能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或者市场化企业的工作压力太大,觉得读博至少可能是条未来前景不错的就业路径。这样的选择有时仍然是由家人或父母推动的,或者是对其他同学的从众式模仿,而其本人常常可能是对未来的学习或工作充满着抵触乃至恐惧,不安全的焦虑感使其常常陷入某种无所适从的压力型“选择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