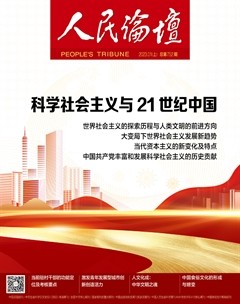【关键词】红色文化 “可沟通城市” 城市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红色文化本质上作为一种精神、意义和价值,具有较强的符号性和较为丰富的传播质素,并且其形成和延续有赖于传播运行。集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媒介化于一體的当代社会,城市化的传播意义和张力得到凸显。有鉴于此,将城市传播视野的“可沟通城市”理念引入红色文化传播研究,有助于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果。
“作为传播的城市”蕴含深厚的人文意蕴
语言转译带来的误解或理解偏差,经由语言“约定俗成”机制的运作,使“传播”一词的意涵被窄化为“中介”“工具”和“控制”,而“communication”原初所具有的丰富人性的“社区”“共享”和“意义”被剥离和遮蔽。同时,从人的社会性本质而言,传播即人之存在本身,恰因其自然性和遍在性而易为人所忽略。由此,随之而来的不仅是传播研究的功利化取向突出,更重要的是大量传播现象、实体、行为和范畴因被无视而难以进入研究视野。加拿大学者英尼斯对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物质的传播意义。后继者麦克卢汉以貌似悖逆常识的“媒介即讯息”的惊人言论,对“物质性传播”进行了充分强调和张扬。以此为背景和旨归,“作为传播的城市”进入人们的视野。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早期城市的经济和政治功能遮蔽了其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传播运行,抑或其时社会的一体化恰是传播的本然状态。古希腊城邦里人民生活的展演尽管显示了作为传播的辩论和修辞,但其要旨和重点关注面向却是民主政治。城市并不仅仅意味着特定地理空间,城市的空间集聚形态是传播内容生产的基础,且空间本身也彰显着某种社会意义。城市的庞大化和复杂化加剧了陌生人社会的形成,由此带来人际传播弱化或缺失,并进而导致孤独、焦虑、惶恐、迷茫等不适心绪,从另一向度提示着城市的传播诉求。
尤其随着基于媒介技术基础上的传媒系统的发展,信息营构的“虚拟空间”(即拟态环境)成为常态化现实,城市作为信息网络的特征更加凸显,亦昭示着“传播之于城市”的本质复归。因此,以传播视野观照城市,城市就是由物质、信息和人及其互动而形成的信息生产和流动空间,由此意义和精神得以生成和丰盈。“作为传播的城市”强化了城市的“属人性”,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意蕴和价值倡导的公共性;同时在理论上拓展了传播研究范畴,形成了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可沟通城市”与红色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为传播的城市”,借用麦克卢汉的表达,亦谓“城市即传播”。在此视野下,西方传播学者提出“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的概念,其基本意涵在于以传播或沟通为城市建设的宗旨理念,吁求以传播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无碍交流和公共性参与。“可沟通城市”将沟通或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性”。
广义上的文化包括物质、精神、行为和生活方式等,而其形成有赖于特定时空维度及其中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频繁互动。红色文化的形成和传承有赖于载体和传播,在此意义上,“可沟通城市”理念与红色文化具有内在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