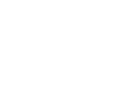1
我要去西藏了,张淼在凤凰园美食城给我饯行。
凤凰园是一家地方风味的连锁店,除了美食城,还有烤鸭店、饺子宴、海鲜馆,位于北新道的美食城是总店,属于综合菜系,口味全覆盖。我赶到时,两个凉菜泡椒花生、糖醋蜇头已经上桌,张淼把菜谱递给我,我看到她勾选了我爱吃的九转大肠、黄花菜小炒,还有她得意的白灼海螺、椒盐大虾,酒是本地产的“渤海纯生”。我把菜谱还给她,说挺好,她憨憨一笑,从主食栏里选了三鲜水饺。
“你怎么不早说?不然,我也想去西藏看看。”张淼的大眼睛水汪汪的,盛满无辜和好奇,就像东北森林里的“傻狍子”。
“还是看我朋友圈吧。”我敷衍道。她爱看我发朋友圈,发表评论时,习惯用那个简洁直观的龇牙表情,就像她平时总爱哈哈大笑,那是人类最没技术含量的笑法。
“去了西藏,你就走遍全国了吧?”她羡慕地问。
“一个人一辈子至少要去两次西藏。”我故作深沉地说。
“为什么?”
“爱旅行的人提起西藏,都会问,你去过几次?而不是,你去过西藏吗?”我干了一杯啤酒,酒太凉,喉咙噎了一下。
“西藏适合两个人去,有个伴儿不好吗?”她直视着我。
去年我去成都,她就想跟我去,说她老公都同意了,并且愿意承担全部资费。“那不叫资费,叫路费。”我纠正她。张淼的老公覃尧在移动公司上班,热衷于推销套餐,动辄赠流量。“他对你的人品太放心了。”当时,她得意地对我说。不知是得意我的人品,还是覃尧的宽厚。
“我习惯了一个人。”我避开她的直视,将视线移向窗外,窗外停着张淼的车,阳光在天窗上打出一个光旋。我眯了一下眼。夏日的午后,北新道有些曝光过度。
每次出游,张淼都执意为我饯行。我居住的港城是个死胡同,出行绕不开市里。有次我从大兴安岭回来,凌晨四点下火车,原想在车站打个盹熬到天亮,不料张淼三点就给我打电话,说她正赶往车站,然后直接把我接到她家,早铺好了一张床让我补觉。一觉醒来,我看见他们夫妇在厨房忙活,大清早就弄了一桌菜。恍惚间,我感觉是住在旅途常见的家庭客栈。覃尧系着围裙煎炒烹炸,看不出有丝毫冷淡,只是酒没喝好,刚一杯就喝趴了,是夜里没睡好吧,要么就是不适应大清早喝酒。张淼对覃尧的窘态视若不见,好奇地追问我:“你在大兴安岭看见狍子了吗?”“傻狍子”是我给她起的绰号,看样子覃尧不知道。他醉眼惺忪,又端起酒杯,一边洒一边敬我,话却是说给张淼的:“张淼,你可真是个好样的。”张淼的这种殷勤令我过意不去,却又不能拒绝,也曾瞒过她一次,事后她反应强烈,埋怨我与她隔心了。好吧,那就顺其自然,麻烦归麻烦,总比瞒着她好。
“听说刚到西藏,有人会因休息不好闹高反,”张淼叮嘱我,“你到了拉萨先好好睡一觉,不能洗澡,更不要喝酒,不舒服就赶紧吸氧,最好是叫医生。”
“应该没问题,我去过玉龙雪山,海拔4506米,下缆车还小跑了一段呢。”
“那是在云南。西藏海拔8848米,差不多高出一倍。”
“你说的是珠穆朗玛峰。”
“噢。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去西藏让人担心。”她问,“你真是一个人去吗?”
“这破啤酒,都是利尿剂。”我放下酒杯,“我还得去趟洗手间。”
张淼哈哈大笑。
在洗手间,我与镜子里那张黑里透红的脸对峙良久,拿不准该不该对张淼说实话。我发觉,与以往的饯行不同,“傻狍子”今天有点反常的警觉。
2
我和张淼是同一年考上的大学生村官。
那个叫亮甲峪的山村,背靠燕山,面朝水库,山明水秀,民风淳朴。村委会开门见山,满目松柏、核桃、板栗和榛子,还有野生山梨、酸枣、不知名的灌木。偶尔还能看见松鼠。
村里没有食堂,我们自己开伙,有时去镇上的餐馆解馋,也经常从水库买鱼涮着吃。张淼爱吃鱼头,她说鱼头健脑益智,我说你这脑子是该多补补了。我爱吃鱼鳔,鱼鳔补肾益精。她哈哈大笑,说你补了也没用。一条鱼我们各取所需,筷子从不打架。这是个天然与我无争的女孩。记得报到那天分宿舍,村委会就两间闲房,一间阴面一间阳面。我喜欢阳面。村主任说张淼毕竟是女性……正犯愁呢,张淼竟主动找他,要求把阴面那間给她。当时我们还不熟,她这么做无关友情。于是我细心留意,发觉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天然地顺应了对方,几乎没有矛盾的交汇点。
清晨我还在昏睡,张淼就砰砰敲门叫醒我去爬山。我们顺着野长城的断壁残垣蜿蜒而上,爬上一座烽火台,鸟瞰被水库淹没的一段城墙。
“鱼做梦都想不到能在长城上游弋。”清晨的张淼特别聪明。
“古代的士兵如果活到现在,也会成为虾兵蟹将。”我也脑洞大开。
傍晚我们沿着水库散步,看夕阳浮在水面,像一个泡得松软变形的蛋黄。“真美啊,真想在这里过一辈子。”张淼张开双臂,那拥抱美好生活的姿势,看上去更像是伸了个懒腰。
“我以为就我一个村官呢,没想到还有你。”她说。
“亮甲峪是文明示范村,省里市里树的典型,又是景区,所以要加强力量吧。”
“嗯,有一只碗我就很满足了,没想到碗里还有块肉。”她说着哈哈大笑,“黎东,你为什么要考村官?”张淼一直疑惑我的选择,她认为那个空气里弥漫着海腥味的港城才是人间天堂,她虽是山里生山里长,却特别爱吃海鲜,有一次我在港城请她,她一口气吃了九只牡蛎。
“我考村官是为了从家里逃出来,越远越好。你呢?”我问她。
“逃出来?”她若有所思,“我好像,也是吧?”
张淼家在县城,父母做生意,公婆家也做生意,两家往来密切,她和覃尧的关系是被上一辈人设计好的。他们考上大学那年,覃尧父母主动来提亲。“我们从小就认识,我还记得他在体育课上尿了裤子。”张淼哈哈大笑,“他个子小,胆子更小,不好意思跟老师报告。不过他脑筋好使。我妈说我傻,找个精明男人不会吃亏。”覃尧工作后,立刻在市里买了婚房,筑巢引凤,只等张淼嫁过去。张淼却以工作不稳定为由一拖再拖,直到考了村官,反而离市里更远了。
“我明白了,你这是逃婚。”我逗她说,“青梅竹马不好吗?”
“我还不想结婚,觉得挺没劲的。”她没精打采地说。
我对覃尧只了解这么多,因为张淼很少提他,偶尔提起,就像在说路人甲。直到那次,覃尧突然光临山村,正赶上我和张淼合伙吃一只烧鸡,张淼将鸡皮撕下来,一片片搛到我碗里。她知道我爱吃鸡皮,而她喜欢吃鸡胸。覃尧在门口站了好长时间,我俩谁也没注意。从那以后,这个长着瓜子脸丹凤眼的美男子就经常光顾了,几乎每次都要留宿。于是就赶上了那场地震。
后半夜,突然地动山摇,虎啸声从地下拱出来,穿透耳膜,如同防空警报。这种地震常有,按专家的说法,统统是1976年大地震的余震。我熟练地一跃而起,迅速拉开房门,下意识地冲向对面宿舍。刚要撞门,门从里面开了,覃尧冲了出来,差点和我撞上。我一时没多想,拨开他的杨柳之躯就往里冲。地震总是发生在瞬间,也在瞬间消逝,人也在瞬间清醒,反应快慢也就是几秒之差。张淼反应稍慢,她刚从床上坐起来,按亮了灯,一脸懵懂地看着门口两个男人,一个面朝里,一个面朝外。我不好意思地朝覃尧笑笑,去了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