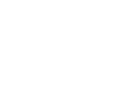一
那个胖子趴在地上,铆足劲,放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屁,身上的衣服、身边的泥土瓦块巴根草被炸得粉碎,在天空飞旋,他光着身子沉到坑里,从屁眼里长出一棵小树。
南蛮子今天心情不错,坐在门槛上给我讲故事。我笑得瘫倒在她脚下,她也笑,露出白森森的细牙。忽然,风暴般,几个人卷地而来落在门前,有人拿出证件,操外乡话跟南蛮子对答,细碎而快,又有本地的警察跟南蛮子对答,神色严峻。南蛮子脸色苍白,嘴唇哆嗦,手哆嗦,身体前后晃荡。
南蛮子跟着那些人下了畈坡,平时走路一颠一颠的左腿,不那么瘸了,甚至健步如飞。过人工渠时,南蛮子打了个趔趄,有人扶住,上坡,钻进一辆深蓝色小汽车里。她要坐车出门了,我以为她会带我一道,至少客气一下,虚虚地邀请一下,我已经做好拒绝的准备。可自始至终,她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爬上门前高大的柿子树,那辆桑塔纳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冲奔而去,身后腾起粗大的黄色尘雾。我看到地里、崖畔、水渠边、草坡上、村巷里,人们在奔跑、汇聚,最后在我家门前汪成一池沸水,咕嘟着气泡,吵吵嚷嚷。
我溜下树,奶奶背着半筐红薯踉踉跄跄地奔过来,一把抓住我,拧我的胳膊,揪我的耳朵:三儿,你哭!你喊!
边上有人说:哭啥?喊甚?人早出了山了,没影子了。
我一声不吭,奶奶自己号啕起来,一屁股跌坐在地,涕泗横流,两只手拍打得尘土飞扬:要了命哪,狠心的女人,不是人啊,猪狗不如!
段家庄二十七户人家,牵牵绊绊都是亲戚。南蛮子是我娘,白皮肤,弯弯的月牙眼,在段家庄辨识度很高。南蛮子不许我叫她娘,我叫她娘,她蹙着眉呲着尖细的白牙骂我,一口又碎又快的南方话,像一条蛇咝咝吐信子。甚至动手,噼里啪啦,下狠劲。
奶奶抢步过来护住我,骂她:虎毒不食子,你比老虎还毒。据奶奶说,我在南蛮子肚子里时,她就做出种种杀死我的尝试,我出生后,她拒绝抱我,拒绝给我喂奶。我拼尽全身力气号哭,放屁,向她请求、示威,她不闻不视。我是喝百家奶长大的,人奶、羊奶。
某刻,我对她生了亲近感,喊娘,她依然又打又骂。我也是痛快人,几次三番,我断了念想,跟别人一样叫她南蛮子。南蛮子,我饿了;南蛮子,给我讲个故事吧;南蛮子,后山沟里的果子熟了……
她呢,叫我“太三”,村里人说像日本人的名字,不如叫兔三。
我会走路后,南蛮子就训练我跑步,她蹦跳着瘸腿,巴掌拍得啪啪响,额头沁出细密的汗:跑,跑,快跑!我跑,跑得快,南蛮子就会潦草地爱抚我一下,对我浅浅地笑。六七岁时,我已经跑得比十岁的孩子快。我成了娱乐的对象,人们无聊了,一脚踢过来:兔三,跑一个。我撒腿就跑,转眼窜出老远,越过沟沟坎坎,跑到对面山坡上,再跑回来。大家兴奋地骂:兔崽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六岁入学,南蛮子在我新领的书本上写下“泰山”两个字,众人这才明白,“太三”原来是“泰山”。笑骂:南蛮子,舌头是直的,不会打卷儿。
南蛮子的种种不友好,让我受到惊吓,产生困惑,却也不是特别在意。南蛮子是一个漂亮而聪明的人,会讲故事,各种故事,尤其关于“屁”的故事。
一个巨屁炸出一个大坑,坑里长出一个肮脏、邪恶的村庄叫段家庄,村里到处是毒虫恶鬼癞皮狗。恶鬼在哪儿呢?我问她。她指点着菜园、沟渠、树梢、屋顶、山坡:喏,这里,喏,那里。
一个白衣白袍骑白马的大仙放了一个屁,满天雪花飘,将女人们的头发染白了。为了佐证,她把头伸到我胸前,果然,她的头发里藏着一缕一缕的白。
一个巨屁,把段家庄炸得灰飞烟灭。
那我们呢?村里的人呢?我问。
炸死了,都被炸死了,一个不剩。她拖着瘸腿,在狭小的院子里来回疾走,像一头困兽,目光灼灼,气喘吁吁。她这么诅咒时,忘了她和我都在段家庄,我们也在冲天大屁中死亡。
现在,她走了,段家庄解除了被炸得灰飞烟灭的威胁。那些恶鬼也消失了,到处是菩萨,面容慈善,目光温和,没人踢我叫我跑一个,没人骂我狗日的兔三,走在路上,经常有人递给我一瓣香瓜两颗野枣。
周一到学校,斜眼女生段春花坐到我前排,看着我的同桌说:你爸死了,你娘跑了,你奶奶生病也快死了,你家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同桌不答话,一巴掌甩过去,段春花嗷的一声惨叫,伸手揪住他的头发。段春花其实是在对我说话,同桌误会了。
课间,几个高年级男生把我围在操场上:兔三,你不是跑得快吗?跑啊,把南蛮子追回来啊。
我背着书包溜出学校,到处闲逛,在山坡上放羊的二爷招呼我:兔三,不上学啦?上学有屁用,不如跟二爺放羊,包你一餐中饭,一天再给你一毛钱。
我扔下书包,坐到二爷身边:二爷,南蛮子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难说。那个女人外地的,根儿不在咱们段家庄,早晚得走,不值得记挂。
二爷指着山坡尽头:南蛮子好几次跑到那里,都被追回来了。
她为什么要跑?
我也不解,有吃有穿,你奶奶待她也好,跑啥呢?能跑哪儿去?荒山野岭,人生地不熟的。
我眯眼远眺,想象南蛮子在山坡上一瘸一拐仓皇逃窜的滑稽模样。
二爷说:咋样,明天来跟我放羊?
我站起来,拍拍身上的草屑,冲二爷一龇牙:放个屁,段家庄就是一个屁。
二
段春花说我奶奶要死了,是胡扯。奶奶体格健壮,跟清瘦的南蛮子比,奶奶就是一座高山。说不清的各种小毛病,对她种田喂鸡洗衣做饭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有一次中了热毒,差点断气,又还过魂来,我学着她的话夸她:福大命大。
春天到了,暖风一波又一波,冰消雪融,大地变得温润柔软。一大早,我和奶奶背着竹筐扛着铁镐和铲锹,爬上村后的山坡,在奶奶选定的地方,凿石掘土,为奶奶掘墓。在段家庄,为自己掘墓与结婚生子同等重要,都是人生大事。活着的时候,在山上选定将来的归宿,掏一个与地面平行的上拱下方的洞穴,拱壁刮削得平整光滑,抹一层水泥。有钱的有脸面的人家,墓穴大而阔,铺上砖石再抹水泥。穴口用石板或青砖封好,将来大限到了,开启穴口,棺材放进去,用青石板封死,刻上碑文,尘埃落定。
这是一项艰难的大工程。我们隔几天上山一次,奶奶说不急,慢慢来,三年五载总会弄好。我说不急,三年五载我就长大了,有的是力气,是本事,几天就能完工,而且建造得宽敞亮堂豪华气派,让段家庄人羡慕死。
两年后,没出正月,墓穴才挖掘一半,奶奶拉肚子,我跑了二十多里山路买了四环素。奶奶吃了药还是拉,瘫在床上睡了一天,夜里咽了气。村长刀疤爷爷——其实是村委会主任,段家庄人习惯叫村长,刀疤爷爷号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出力的人多,出钱的也不少。原来奶奶借了那么多债,债主们一脸焦虑,围着刀疤爷爷诉苦。刀疤爷爷说大家都不富裕,谁家日子都不好过,再不好过也得先把眼下的丧事办了,欠谁的,欠多少,以后再说。
我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段三总有长大的一天。
一片沉默中,段春花爸爸表态:欠我家的十二块钱,我不要了,算出份子钱吧。众人纷纷仿效。只有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段荣志拿的是现金,两百元,段荣志父亲瞪着他,脸上青红黑紫地变换。
家里三只羊,我挑了一只送给刀疤爷爷,刀疤爷爷坚辞,我反复表明是请他代养,他才收下。另外两只卖给二爷,十来只鸡鸭鹅婶娘们分了,门前屋后的柿子树枣树二十块钱一棵,都是市场价,大家没少给一分钱。庄稼地和菜园,谁种谁收,反正我也不会种地。
我想把墓穴抢工挖好,把奶奶送到山上去。刀疤爷爷说三儿呀,不是大伙儿不帮你,时间来不及,就葬在你家畈坡下面的菜园里吧。
我不说话,趴下磕头,磕响头。
刀疤爷爷叹了口气,叫上二爷,两个人把山脚下村里废弃的红薯窖清理了一下,奶奶便入住了。
二爷说:人死如灯灭,山坡山脚都一样,都是入土。
我附和道:就是,以后扫墓,还不用爬山,我奶奶想回家看看也方便,转身就到。
所有人都不提我还有个娘,仿佛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想跟谁聊聊南蛮子,那人要么惊慌失措岔开话题,要么劈头训斥:什么南蛮子不南蛮子,你小子生是段家庄的人死是段家庄的鬼,你段荣贵三个字是记在段氏族谱上的。
户口本上,我不叫泰山,也不叫兔三,叫段荣贵,白纸黑字红印章,鼓荡着对荣华富贵的隆重期盼。
我出生后,奶奶请段家庄高级知识分子段荣志为我取名字,段荣志是我远房堂兄,村小代课教师。段荣志为我取名“段炼”,我奶奶谢了他,结果户口本上写的是段荣贵。段荣志很是痛心,就将段炼做了自己的笔名。他是一名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他揪头发抠脚丫捶胸顿足绞尽脑汁创作出来的豆腐干,一篇没发表,一摞一摞,锁在抽屉里,发酵成了豆腐乳。
南蛮子走了,奶奶死了。我像平原上的风一样无拘管,我在床上睡觉,在板凳上睡觉,在地上睡觉,然后,村里村外到处晃荡。
我得干点儿什么,干点儿大事,让段家庄男女老少对我刮目相看,承认我段三是一个重要存在。
我白天黑夜潜伏在段家庄各个角落,偷瓜摸枣,拔公鸡毛,往酱钵里撒尿,用烂泥糊死大门上的锁孔,把癞蛤蟆扔进人家窗户……村里的猫狗都怕我,看到我,绕道走,实在躲不过,冲着我龇牙谄笑。
人们不叫我兔三了,叫我天罡星。
天罡星也是段家庄的天罡星,总有人在我饿得不耐烦、将死不死时送饭过来,妇女们隔三差五帮我洗衣缝补,二爷教我放羊,段荣志揪着我的耳朵押送我上学。
那天,我将一把苍耳揉进斜眼段春花的头发,段春花撕扯着自己的头发,骂我是杂种野种。我一时兴起,索性撒了个野,把教室里的桌子板凳乒乒乓乓推倒,把粉笔黑板擦扫帚洒水壶扔出去。段荣志在全校师生的呐喊声中,绕操场追了七八圈逮住我,拎着我破烂的衣领,把我揪进他破旧的办公室兼寝室,等气喘匀了,狠狠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被锁在屋里写保证书,写二十遍。
段荣志离开前,警告我不许乱动。警告往往就是启示,我揭开电饭锅,锅底结着厚厚的底子,一股馊味儿;掀开被子,斑斑污渍。我撬开抽屉,一抽屉信件,收到的,待发的,五花八门。
有一封信贴了邮票封了口,没有发出,收信地址是南方某地,收信人水国庆。居然有姓水的,咋不姓尿呢。我扑哧一笑。那个地址似曾相识,略一想,是南蛮子说过的,南蛮子除了讲系列屁故事,还讲志异人物,开头总是:在长江南岸某省某市某县。某省某市某县跟信封上的地址一模一样。
原来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大为惊异和兴奋。
我关上抽屉,锁好,认真写保证书。下课了,段荣志进屋,把书本重重地扔到桌上,绕室内转了一圈,未发现异常,坐到嘎吱响的木椅上,端起茶缸咕咚咕咚一番牛饮。
我站得笔管条直,呈上保证书:段老师,我今天才知道你真的有才华!我指着满墙的名言警句雄文华章: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都会背了,你的才华被埋葬了——
没,埋没。
对,埋没,你的才华被埋没了。他轻轻地放下茶缸,抬起头,目光亮了一下又暗淡,明明灭灭,像电压不稳的灯泡。
段老师,不,你是段炼,伟大的文学家段炼,你是段家庄的人种,是人中龙凤,我们为你欢呼为你骄傲。
段荣贵按着桌沿缓缓站起来,伸出右手,我以為他又要抽我,却是为我擦嘴角的血迹,手指上的粉笔灰红墨水抹了我一脸。
段荣贵,你是个聪明的家伙,遗传了你娘,除了我,你是段家庄最聪明的,你怎么就不学好呢?
我娘——我舔舔唇边的粉笔灰:我是说南蛮子去哪儿了?她还会回来吗?什么时候回来?话一出口,我就后悔,问得急了。
果然,段荣志脸色一凛:她要回来,河水就倒流了,这个女人不是人,往后不许提她。
不是人,就是被开除人籍了,就像学校开除学籍,是吧?她既然不是人,那她是成神了还是成鬼了?
成鬼,鬼都不如。段荣志斩钉截铁。
她那么瘦,瘦得像高粱秆,面皮白石灰似的,整天吊丧着,走路还一瘸一拐,可不就是个白无常吗?我哈哈大笑,且笑且退,出了屋,出了校园,出了段家庄,出了重重叠叠的大山。
再回段家庄,已经七年后。
三
2001年儿童节前夕,高空坠物般,我突然坠落在南蛮子面前。我不看她的惊恐、惊惶,我亲亲热热地叫她父亲外公,叫她哥哥大舅,好像和他们早就认识,一直生活在一起,毫无违和感。他们尴尬地小声应着,脸上的表情渐渐舒展,目光里有了暖意。
南蛮子还过魂来,竖起食指,目光严厉,不许我靠近。
外公说,十岁大的孩子,一个人千里迢迢寻来了,没丢失,没饿死冻死,没磕着碰着,全羽全须地找到这里,难得了,也是天保佑。那边也没有亲的疼的,你让他一个小孤儿往哪里去?不管怎样,先住下来吧,其他事慢慢说。
大舅给我洗澡,带我出去理发,买衣服。
我跟外公、南蛮子住在单门独户的老屋里,大舅一家三口住他们单位早年的集资房。老屋是平房,有个小院,坐落在环城河边一块叫“泰山头”的高地上,这也许就是我“泰山”名字的由来吧。
他们以为我也许待一段时间就回段家庄。两个月过去了,我从不提段家庄,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回段家庄的意思,我眼皮薄,手脚勤快,脑子转得也快,每天快快乐乐一副笑模样。
我背着书包,步行,坐车,三轮车拖拉机中巴大巴卡车火车出租车摩托车,还坐过轮渡。钻各种各样的栅栏,爬高高低低的墙,睡不同的地方,车站桥洞草垛木棚水泥涵洞。相比睡觉,吃饭比较容易,无论在哪里,总有人给我一口吃的,有时给我一大包吃的,差点消磨了我南下的意志。我就这么游著荡着,向南方前进,有时坐错车,折回几十里、上百里,弄清了方向,再进发,毫不气馁。辗转二十七天,才来到段荣志信封上、南蛮子故事中的这个叫“濡江”的地方,怎么能轻易回去呢。
南蛮子不许我出门,尤其是跟她一道出门,不许我叫她娘,或者妈。
我叫她“哎”。不能叫南蛮子了,这里是长江之南,所有人都尖着舌头说话,又碎又快,丝丝缠绕。吃的是稻米、水磨团子、菱角粽子、桂花酒酿小元宵,喝本地产的绿茶,都是南蛮子,我不敢触犯一个地域的人。反倒是,有人叫我“小侉子”。
大舅托人把我送到最近的学校读五年级,学名叫泰山,不姓段,也不姓水。两年后小学毕业,学校发了毕业证书,填的在校学习时间是“2001年9月—2003年6月”,我人生中的第一张学历证书是残缺的。
外公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我们捧着毕业证书和美德少年、三好学生的奖状回家,外公笑呵呵地对南蛮子说:看,泰山多聪明,多厉害。晚上,外公炒了几个菜,在柜子里掏出一瓶放了十多年的白酒,说好长时间没喝酒了,今天可得喝两杯,祝贺你呀泰山,泰山你好好读书啊,将来考大学考博士。
我睡觉了,外公还在喝。第二天早上,外公没有起床,再也没有起床,大舅和南蛮子把他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奶奶和外公的去世,让我认识到死亡跟放屁似的,是一件很草率、随意性很大的事,一个活生生的人,睡个觉就能睡死。从此,我对睡觉充满警惕,经常半夜惊醒,检视自己是否活着,侧耳倾听南蛮子是否有声息。
外公不在了,南蛮子不肯和我多说一句不必要的话,必要的话又总是那么少。泰山,兔三,段荣贵,她从来没叫过我一声。她敲筷子、敲碗、敲桌子、敲凳子、敲门和我交流,或者作为交流的前奏。如果手边没有可供敲击的东西,她先咳嗽,引起我的注意,然后开口。
两个人的屋子里,宇宙洪荒。
九月,我进入附近一所中学读初中,还是没有学籍,借读。我没有出生证,没有独生子女光荣证,没有疫苗接种证,没有户口本,没有身份证,是一个透明人。大舅托了人,说我这种特殊情况,只要本人愿意,可以把户口迁过来,建立学籍。我不愿意,我相信自己迟早要回段家庄。南蛮子也不愿意,拒绝在户口本上与户主关系那一栏填写“母子”。
她跟我不是母子,跟其他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亲人。流浪的小猫小狗来了,她挑选边沿破损的碗,放在门口,给它们喂食。蜻蜓落在水洼里,她捡起一根树枝捞起来放飞。雨天,蜗牛满地爬,她挪走路上的砖石枝叶,清理障碍物,让蜗牛爬得快些,好像它们正在逃离危险。一只雏鸟摔死在院子里,她给埋在梅花树下,碎碎念念说了一堆话。
有一点必须承认,尽管嫌憎我,南蛮子一直在努力养活我。
她心灵手巧,在家织毛衣、织渔网、做雨披、绣花,用碎布丝带钉珠编织工艺品,外公去世后,她靠编织绣花挣来的钱填不饱我巨无霸的胃口,她抹下脸面,走出家门。虽然腿有点儿瘸,不妨碍她行动敏捷,她做过酒店服务员、超市营业员、医院保洁员、幼儿园食堂洗菜工。做一段时间就辞工。她对每个人心怀戒备,人家小声说话,她认定是在议论她;谁多看她一眼,那个人必是心怀鬼胎,图谋不轨。
她摆过水果摊、旧书摊、卖袜子拖鞋的地摊,每次都是草草收场。
后来,她去人家做钟点工,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干完活儿就走,不用跟人打交道。她勤快,手脚干净,从不偷奸耍滑,在业内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同时做几家。晚上和休息日,继续在家做工艺品。
南蛮子这么勤劳,我却一直饿,肚子里总空着一大块,我想吃肉。
濡江地处长江岸边,水多,水产品丰富,有的是鱼虾鳖蟹黄鳝田螺河蚌。南蛮子不吃肉,爱吃水里的东西,尤其是鱼,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鱼。大鱼很贵,通常只买些小鱼小虾。她吃鱼从来不卡刺,无论多小的鱼,她都吃得肉是肉刺是刺,仿佛舌头上长了眼睛。
南蛮子不吃肉,我一吃鱼就卡,所以,我们的荤菜以鸡为主,散称的鸡翅、鸡腿、鸡胸脯、鸡爪子,南蛮子烧好了,自己很少动筷子。吃鸡多是节庆日,平时,我们主要吃蔬菜,吃杂酱,黄豆、干子、小米虾、胡萝卜丁和豆瓣酱烧出来的杂酱,一天三餐都能吃。
我想吃肉了,就去大舅家,大舅会特意做一大碗红烧肉,有时做糖醋排骨。我一个月去三四次,每次寻个理由。我是个有尊严、要脸面的人。
春天,大地上,一大片嫩绿一大片明黄一大片艳红,蜂蜂蝶蝶,飞来舞去,叫人心烦意乱。那天,南蛮子捧着大瓷盆和面,我走到她面前,喊了一声“妈”,跟叫很熟悉的人张三李四一样自然,她抬起头,恍惚了一下,嘴巴微微张开,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神志不清的鱼。
她惊吓的样子让我有点慌乱,我心一横,索性坚定地看着她的眼睛,又叫了一声:妈。
她放下右手的筷子,一掌甩到我脸上,又准又狠:我警告你,不许叫我妈,我不是你妈,我从来没结过婚。
我退后一步,声音高亢强劲,像沾了芥末:妈。又退后一步:妈,妈。
她抄起桌上的长柄铁勺,我夺门而逃,她气急败坏的骂声从背后追杀过来:疯子,傻子,滚,滚走,滚得远远的!
此后,只要某个场合只有我们俩,我就冲着她叫妈,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饱满,一边喊,一边殷勤地送上脸,方便她抽嘴巴。渐渐地,她不再打我,一声不吭,转身就走。
她对我的无视,让我觉得自己是一小片虚空,是一缕空气,是一个屁。
三八妇女节那天晚上,她下班回来,先插上电饭煲热饭,然后站在厨房的水池边刨土豆皮,我铿铿锵锵地走近她,郑重地宣告:我要走,要离开你。
她不說话。我嚷道:听见没?我要回段家庄。
她头都不抬:什么时候走?
我有点吃不准她这么问的意图,稍稍犹豫了一下:下个星期。
用得着下个星期吗?没有什么东西要收拾,又没有亲的疼的要告别,为什么不是明天?不是现在? 现在就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