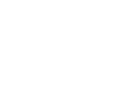春日昏昏,除了枕着美梦呼呼大睡,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手摸床头的手机,不出意外,新闻又为我打点好了一天的愁云苦雨。楼下的两株海棠树,花比往年开得早,谢得也早,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春雨洗劫,粉红的颜料抖落了一地。我有的是抖不掉的胡思乱想,于人世安泰无益,更于心肝脾肺无益,只好做点什么转移注意力。
德国人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这个因疫情而变得灰色的春天,诗没写半句,却和朋友合谋干了件更没谱的事——写歌。
磨刀霍霍,历时两个月,一首名叫《不凡》的歌曲终于“杀青”。歌名是曲作者“乡村耳机”特意改的,原名叫《理想的马》,更像一个庸俗的散文标题。我说改得好,歌是让凡人听的,名字就得利索,通透,直抵本心。面对乌泱泱的人间面相,修辞的小伎俩,同样也是残忍的。
对乐理一窍不通,令人艳羡的音乐细胞都幸运地长在别人的身体里。流行音乐从小听到大,耳朵忙着享受,脑子就落得很清闲。有一点从未琢磨过,那些婉转动听的旋律,看不见又摸不着,好没影儿的,怎么就凭空从别人的脑子里冒了出来,并且被一些语词勾勒出了如此可触可感的迷人容貌呢?
台湾创作人李宗盛曾用了十年的時间来为一段旋律赋形。这股旋律起初在二〇〇三年夏日的一天来到他的耳边,可是直到二〇一三年才凭借着《山丘》的名义面世。十年是一道如此宽阔的鸿沟,世事沉浮,人在年岁的磨砺中一点点地陈旧,词与旋律都不着急,它们幽居在一个人的头颅中慢慢发酵成型,它们在等待一个共同的天赐良时完成命定的交汇。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时不我与的哀愁……”印象是二〇一五年的春天,在诸暨乡下一个尘土飞扬的工地采访完,返回杭州的途中,我累得歪倒在后座,四顾惶然,这首歌不期然地从车载音响里飘了出来,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那年我二十五岁,理论上,还远未活到够格听李宗盛的年纪。
记得有人说过的,音乐是神的语言。那么,作曲家就是神下派人间的使者吧。
好多年前,我的朋友昌有给自己取了个“乡村耳机”的网名。他相信自己生来就是神的诸使者之一。这顶虚拟的耳机,兴许就是他和神秘密联络的工具。想想,至少有十年,神没给他传递半点音讯了。曾经,他和神的关系是如此亲密,通讯是如此频繁,不舍昼夜。
我是亲眼见证过的,在我们寒窗苦读的中学时代。他抽屉里夹着一个青蓝皮的本子,上面填满的,除了青春的激扬文字,还有一页页比数学公式更晦涩的曲谱。天不垂怜,打小不识谱,代表音符的七个数稍一颠倒组合,我的舌头就跟着打结。昌有不同,他天生禀赋,不仅能读谱,还能把随口哼出的旋律翻译成乐谱。大学时代,有了更多空暇,他自学作曲编曲和声与后期制作,创作了数十首各类风格的歌曲,有校园民谣有摇滚,也有RAP,不一而足。
那些年里,昌有昂着骄傲的脖子,无师自通地耍着音乐的十八般武艺,没日没夜地向我们宣读着“神的懿旨”。
可是,就像谁也说不清MH370如何消失的一样,我也没法向你解释,为何大学毕业之后他的音乐灵感一夜之间就蒸发殆尽了。此后将近十年,他再没写下一首歌。属于他的神,没打一声招呼,躲进了云深不知处。
这些年我逢人就说,昌有把他最巅峰的音乐才华都贡献给了我。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结婚、儿子诞生,都有他的音乐亲临现场。一首是《结婚快乐》,一首是《了了》,曲风无华,却因真挚的情谊分外抓人。在我儿子了了长到七八岁的年纪时,我第一次把这首歌放给他听。他瞪大了眼,耸着尖尖的小耳朵,一遍遍抚摸着这支欢快的曲子,吃惊于自己甫一降世便被人写进了歌里。一个孩子的惊喜哪里藏得住呢?对他来说,这支歌的出现,如同意外的荣耀加身,让他在学校里昂首挺胸了好一段日子……
昌有比我勇猛,身居困顿的现实,他居然敢先后两次成为别人的父亲。他的双手环抱着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孩子,自然就没了抱吉他的时间。十年里,他先后买了三把吉他,都是雅马哈牌子的。他摊开双手抱吉他的样子,就像抱着自己的灵魂伴侣。这些年,他抱孩子的间隙当然也抱吉他,只是有点心猿意马,扫出的一律是别人的和弦。每年春节在老家相聚,我都忍不住怂恿他:昌有,写吧,多写点歌,不要浪费了才华。你完全可以出专辑,当一名歌手!他嘴角露出神秘的一笑,说时机未到,尚欠火候。
相信我,当年他可不是这种委婉推托的语气。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替他记着呢,在二〇〇七年某个清早的南康中学寝室里,大家伙被广播里的《霍元甲》叫醒。起床后,昌有来到墙角的立镜前,先习惯性撩了下额际的一缕刘海,然后豪气万丈地向众人宣布:给我十年,保证超越他!很遗憾,十五年一晃,那个神话般的“他”就算已经懒到了半退休的状态,至今仍然未被一人超越。
时间赐予了昌有过多的谦逊,同时也剥离了他身上一度可贵的锋芒。
我还是不厌其烦,逮着机会就怂恿他写歌。虽然,自己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年涂鸦不了几行字。我说别等了,明日复明日,就现在,你作曲,我来填词,给这死水一潭的生活搅点动静。我哪里会想到,这次他表面推诿,事后竟暗渡陈仓,不到十天就发来了一支哼唱的DEMO。听了几遍,觉得有模有样,副歌尤其带感,激昂的旋律背后透着一股人世沉浮的苍凉感。我说有了,就写写人到中年的感受吧。他当即和我隔空击掌,说想法不谋而合,曲子的灵感就是清早在卫生间洗漱照镜时忽然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