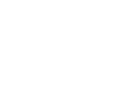这个夏天发生了很多事。其实也不算多。鸡毛蒜皮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这便算不得事。真正勾起人回忆的事,总和生死相关。所以关于这个夏天,阿兰只记得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阿兰得病了。不知道是什么病。可能是疟疾或是白血病,阿兰依稀记得这两种病会便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线索。她整日惶恐,只好把卫生纸垫在下面,隔几个小时就去一趟厕所。她觉得自己好像时日无多,也不敢跟家里人说,也不敢让他们察觉。这一定是什么大病,不然也不至于流血不止。至于是白血病还是疟疾就无从得知。
这种现象持续了三天,阿兰写下了一封遗书。仿照电视剧里的情节,她郑重地写下: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弟弟、爷爷、奶奶,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很后悔,没有听你们的话,认真学习,可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爸爸妈妈,真的对不起,以前我总是去别人家玩,没有好好帮你们做事情。在书柜第二层的盒子里,有我存的十一块钱,你们记得拿去。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好好的,要健健康康,要活到一百岁……
她还要很多话要讲,可又写不出什么来,眼泪落地比字还快。哭了一阵,又觉得一直哭不好。于是她冒着鼻涕泡,郑重地把这封遗书放在书柜二层的盒子里的最下面,上面是她收集的卡片和贴纸,还有整理在一起的一角、五角的纸币。她一边藏,一边抹眼泪。
大家坐在一起看电视时,弟弟和爸爸照例争抢遥控器,她完全没有心思参与,只是一动不动地难过又烦闷地坐着。她和周遭的一切仿佛格格不入了起来。爸爸说,乾京去给我倒杯水来。弟弟说,我在看电视,你自己去呀。爸爸又说,老二去给我倒吧。阿兰嗯了一声,僵硬地起身去了。突然弟弟在背后大声地说,你屁股后面有血。阿兰脑子一下子嗡嗡地响,她僵硬地转身,站在那里,手指头抠着裤缝上的线头。
她听见了笑声。可她笑不出来。
妈妈说,你是来了月经,快点去换掉裤子免得裤子染坏。拿卫生巾去换,你知道怎么用的吗……她不记得自己是点头了还是摇头了,那种恍恍惚惚的状态一直缠绕着她,她在厕所里待了很久,看着裤子上鲜红的污渍,她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为什么她不是男孩子呢,男孩子一定没有这些烦人的事情……出了厕所,她坐到椅子上,妈妈说,你现在不去把裤子洗掉吗,等到血浸到布里就洗不掉了。她拿着换掉的裤子出门去洗,听着屋里的人在讨论现在的女孩子这么早就来月经,以前的人都是十五六岁才来的,她听见三婶在大声地说,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吃的东西净是激素,还有什么地沟油……
夏天来势汹汹,又让人猝不及防。炽热的温度裹挟着风,风变得绵软灼热,吹得人心中燥热。阿兰用力地搓着裤子,哗哗的水将血色晕染淡化,带着腥气的水在发白的水泥地上留下深色痕迹。她的汗水一颗一颗地冒出,有的滴进水里,消失不见;有的啪的一声,独自晕开一个点,又很快干掉。她用胳膊狠狠地擦着汗,把裤子晾到竹竿上。
水分逐渐蒸发消散,只留下了似有若无的血腥气,怎么也散不掉。她突然想起什么,冲进屋子里,把那封她认认真真写下的遗书撕掉,扔进了水沟里。
第二件事情是阿兰的奶奶廖太婆不好了。廖太婆不知是为什么不好,只觉得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于是整日整日地呻吟着。以前阿兰经过她的房间时,只是快步走开。现在,阿兰不怎么经过那扇门了。但她还是整日呻吟。叫声断断续续,从床板上传来,跨过高高的门槛,经过前院,顺着马路,断断续续地窜进过路人的耳朵里。刚开始,大家觉得好奇,并且觉得可怜。后来大家便厌烦了。到了夜里,村里女人同男人讲闲话的声音,断断续续,穿过房门,出了院子,顺着马路,断断续续地窜进廖家人的耳中。
廖太婆的儿子们会了面。
大儿子说,必须要把娘送去医院看看,做个检查也好,要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二儿子说,送是要送的,哪些人去呢?
三儿子说,我家里有个板车,可以用板车送过去。
四儿子说,那就這样吧。
最后大儿子拍了板,那就老三老四去,反正要走个形式。
其他三个儿子都说,是,要有个形式。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空气带着微微的湿润。村子里最先醒来的是狗。只要有风吹草动,或是路人经过,狗就会自发醒来。一只狗叫起来,就会有千千万万的狗呼应。村子里没有那么多狗,但那狗叫声却真是有千军万马的气势。于是公鸡也醒了。天边泛出微微的光亮,公鸡开始打鸣。狗叫声短而急,公鸡的叫声悠长。在这背景声中,酣睡的人也醒了。
八月的稻田像油画似的,一块一块,拼接而成。色彩浓郁,绿得醉人。这绿色和绿色之间,又略有差别。有的深,有的浅,有的业已泛黄。
阿兰和三婶推着板车,走在马路上。两边是片片的稻田,过不了多久,田间就会洋溢农民的笑声。两家的男人因为有事,最后并没有出面,只是各派了代表。阿兰就是老四家的代表。
阿兰的奶奶半躺在板车里,起了毛边的大草帽遮住了略微刺眼的阳光。她轻声地哼哼,过路人都回头看。
阿兰是个拘谨的孩子,对旁人的目光很是敏感。她控制自己的眼神不飘到旁人的脸上,可是旁人的眼神肆无忌惮地留在她们三人的脸上。她步子迈得很正,装作目不斜视,挺起背,但是一下子就塌下去了。
下头黄家院子的人也从屋里出来看,有些人吃饭吃得早,手上还端着碗,看到三人经过,饭也不吃了。
这是去做什么?
送老人家去看病嘛。她总是不好,我们也去看一下到底是哪里不好。
哦,难怪。确实,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容易不好。去看一下也是安心。
老人家哪里不好啊?
不知道,老人家自己也讲不出是哪里不好。看医院里怎么讲。
……
阿兰边推车,边竖起耳朵听这些大同小异的对话。
到了镇子上,医院还没开门。住在边上的一个男人正在洗漱,白色的泡泡吐在了地上,薄荷的味道和阿兰家里的是一种,他又含了一大口水,仰头嗬嗬地漱口。漱完了口,又走进屋里拿出洗脸帕,对着水龙头打湿,也不拧干,直接擦脸,动作简单粗暴,像是搓澡一样。把帕子洗了一遍,又晾回衣架上。他家里女人是在炒菜,而且是在炒酸萝卜,酸味喷薄而出,交杂着肉香。阿兰下意识吞了口口水。
你们这是做什么,老人家哪里不好啊?他看到三人,问道。
就是不知道哪里不好才过来看嘛。老人家年紀上来了身体不好,过来做个检查开点药才安心。三婶接过话茬。
那你们一路上推着老人家过来的?这么远,确实还是孝顺。老人家有福气。
三婶原本的笑容更是灿烂了,嘴巴咧开,回答他,是你讲话这么中听。做子女的,老人家身体不好,看还是要看一下的,尽一下孝心也是。讲着是大半辈子受苦受难,到了晚年也要安心过不是。
那确实是,现在好多年轻人到外头去了,几年几年不回来,大人在家里身体不好也不知道。我平日里也说还是要多关心点老人家,毕竟年纪这么大了,也不晓得还有多久的时间。男人照例寒暄了一段,又问,老人家年纪多大了。
明年就七十了嘛。
噢,你们是打算住院?
还不晓得,要看做了检查之后医生怎么说。要开药还是住院,反正看情况定。
那你们稍微等下,现在开了门,但是医生还没上班。
等下倒是不要紧,反正检查是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