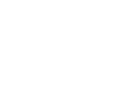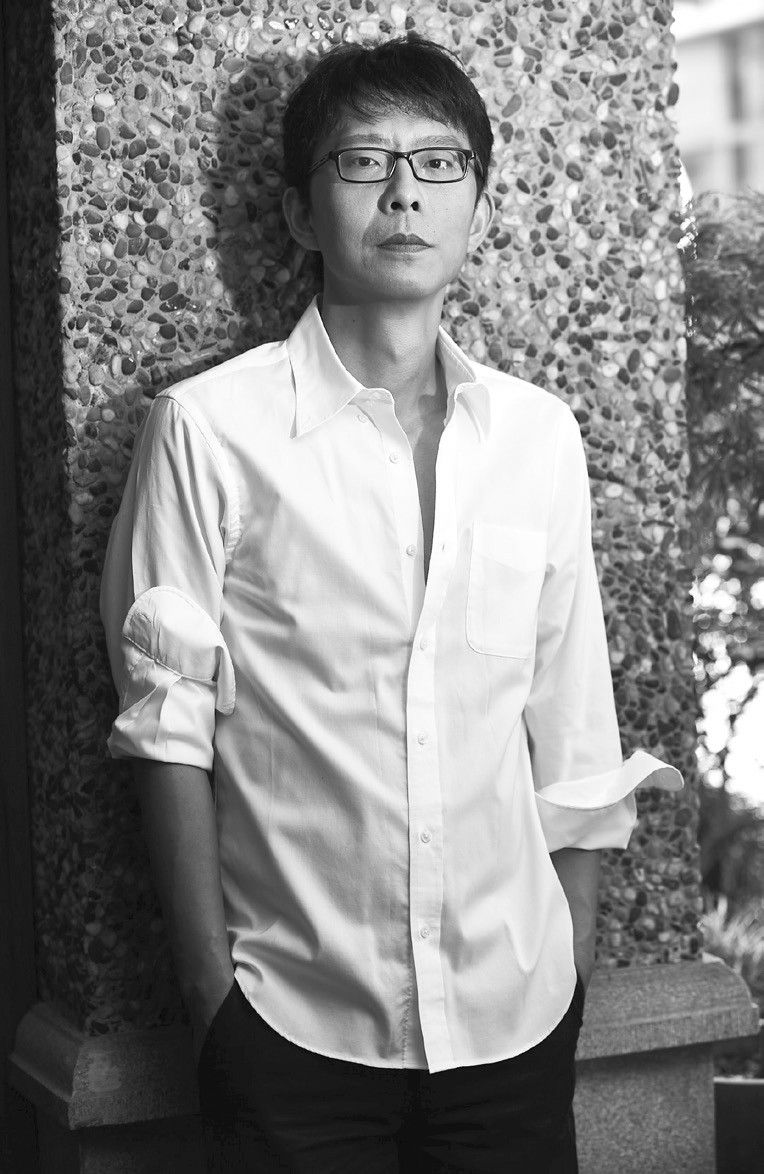
在今天这样一个危机四伏乃至于思想和行动都陷入瘫痪的时代,阅读几千年前的《诗经》不应当视为一种逃避,相反,它关乎理解力的培育。这种理解力,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绝非一种中立的观念,而是我们用以应对种种史无前例和荒诞不经之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令我们得以“自觉地审视和承担时代给予我们的压力——既不能忽視它的存在,也不能屈从于它的重压”。比如,在阅读《小雅·正月》这首长诗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西周末年的诗人如何去理解他所身处的黑暗时代,这种理解力,既是对现实的正视,是对境况真相的还原和对后果的描述,它本身也是个体在面对时代和自身危机时所能做出的所有抵抗的源泉。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和现在的农历正月不同,这首诗中的“正月”自汉代以来就被解释为正阳之月,即夏历四月,也就是今天的农历四月。这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孟夏时节,本不可能出现繁多的霜降,因此“正月繁霜”是罕见的灾异之象,故君子忧之。到了近代,渐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只是汉代阴阳家的附会之说,如高亨就认为“正月”不能被解释为正阳之月,这里只是“四月”的抄写之误;俞樾则认为“正月”就应当表示岁首之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就是常见的对于春节前后阴冷气候的感慨。但这两种解释,都缺乏强有力的文献证据。我们知道《诗经》解释中的分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的毛诗与三家诗之间;二是宋代朱熹《诗集传》和毛诗之间;三是清代训诂学家与汉学、宋学之间,但在“正月,夏之四月”这个判断上,无论是汉、宋还是清,绝大多数学者竟然都保持惊人的一致,所以在没有绝对明确的新证据之前,我们还是应当依从旧训。
繁霜,频繁降霜。《周易·坤卦》初爻辞:“履霜,坚冰至。”君子见微知著,脚触秋日初霜即感坚冰之气息,何况于春夏之际遭遇繁霜。“我心忧伤”,既是对此刻天灾之忧,又是对即将到来的更大祸患的担忧。
“民之讹言”,一直有两解,一种认为是来自小人的奸伪之言或妖妄之言,带有强烈的贬斥之意,如欧阳修《诗本义》,“‘民之讹言’以害于国,又甚于繁霜之害物也”;另一种认为指民间谣言,是较为平和的中性表述,如李元吉《读书呓语》,“《正月》诗之‘讹言’,盖后世谣言之意,言国将危亡,非奸恶之言也”。就诗意而论,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好一点,因为给一个国家造成实质性危害的,永远不是言论。
《正月》这首诗,大抵写于西周将亡未亡之际。此时一个庞大的帝国行将倾覆,上下失序,必然谣言四起,这些谣言即便不是真的,也是民众情绪和心理的反映,正如孟夏时节的霜降,虽或属偶然,但执政者也可以借此罕见天象来反省自身,若是单纯地将之斥为奸伪、妖妄,就好比动辄将一些正当情绪的反映归诸敌对势力的撺掇,用敷衍了事的方式去对待沸腾民意,只能加剧谣言的进一步扩大。“亦孔之将”,孔,甚也;将,大也,表示方兴未艾之趋势。“亦孔之”这个句式还散见《诗经》多处,是一个常见的副词修饰形容词的结构,比如本诗第十一章就还有“亦孔之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的意思大致就是,来自民间的谣言,也愈演愈烈。
“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在变幻莫测的天灾和盲目汹涌的民情面前,每个清醒者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京,大也;忧心京京,形容自己忧愁之广大,不单为己身而忧,更为社稷、为生民而忧。我的孤独无依和我忧愁的广大,形成鲜明对照,一如帕斯卡所谓“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但这广大的忧愁却无法公开,只能小心翼翼地藏在心中,因为在黑暗时代中首先丧失的就是允许人们自由交流的公共世界。癙,旧时注家都语焉不详,今人赵雨和卢雪松所撰《〈小雅·正月〉疾病名义考》认为就是鼠瘘、瘰疬之病,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讲,就是颈、腋处的淋巴腺结核,中医认为多为愤懑郁结所致。痒,与疡通,有疮口之意。癙忧以痒,指的是忧郁情绪导致的淋巴腺结核自行溃破,疮口难以愈合的样子。这第一章的末两句诗,是诗人叹息并描述自己谨小慎微、郁郁成疾的惨况。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这里的选字有押韵的考虑。愈愈,古训为“瘐瘐”,也是疾病的意思,但朱熹《诗集传》据苏辙《诗集传》认为这里的“愈愈”可以就从字面解释为“益甚”,就诗意而言似乎更为通透。这一章的前两句诗顺承第一章末句而起,询问自己的疾病因何而起。“父母生我,胡俾我瘉?”旧解多认为这是对父母的埋怨,埋怨父母既然生下我为何还要使我患病,但这样解的话,后两句“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的主语就变得迷离起来,如果主语是“疾病”或作为疾病隐喻的“虐政”,即埋怨这疾病或虐政既不在我之前发生也不在我之后发生,正如孔颖达所指出的,“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况以虐政推于先后,非父祖则子孙”,这种埋怨似乎有违君子常情,孔颖达的开脱之词是“穷苦之情,苟欲免身”,也就是说诗人被逼急了没办法只求自保。但这种开脱,似乎也小看了诗人。
我的身体发肤来自父母,但我现在的郁郁成疾并非遗传基因所致,“父母生我,胡俾我瘉?”正是用反问的方式明确否定了父母作为疾病的来源,而那使我生病的人既然不是父母,那又是谁呢?显然是朝廷上具体的奸邪贪腐之小人。这答案呼之欲出,又不曾明说,正是诗人的“哀我小心”。由此,后面四句便豁然贯通,“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这连续由“自”字串联的四句,其主语原来都是诗人通过前两句引而不发的“小人”。这些小人不在我之前出现,也不在我之后出现,(就恰恰被我遇上),他们一会说些冠冕堂皇的好话,一会又说点色厉内荏的恶语,(但都与真实毫无关系)。“忧心愈愈,是以有侮。”国家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而对于像我这样独抱深忧的人,他们只会视为迂阔而加以戏侮。
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前两章末尾处重复出现的“忧心”,在此章被忽然提至首句,诗人于此章重新审视自己的忧心,并一一列举所忧之事,从一己之身至黎民百姓,再到整个国家的前途。惸,又作茕。惸惸,孤独无依的样子。怀抱深忧之君子面对一众小人的欺侮,自然是孤独的。无禄,即无福,不幸。诗人感慨自己不幸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这两句如何解释,历代多有分歧,相较而言,似乎还是朱熹解得较为明晰,“古者以罪人为臣仆,亡国所虏,亦以为臣仆。箕子所谓‘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是也。言不幸而遭国之将亡,与此无罪之民,将俱被囚虏而同为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哀叹我们这些人,又将从哪里得到福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对于这两句中乌鸦栖屋的寓意,前人也是众说纷纭,钱锺书《管锥编》引张穆的说法,认为这里的“乌”当指“赤乌”,是“周室王业之征”,可谓深切著明。它曾经聚集在周武王的屋顶上,被视为祥瑞之兆,而如今,西周即将沦亡,这些乌鸦又将栖息到何处呢?这也就是在问,这个偌大帝国的命运会落向何处。这一章讲清楚了诗人之忧是亡国之忧。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这首诗的前几章,每每于次章开头申发前章末尾未尽之意,如第二章开头的“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就是从第一章末句“癙忧以痒”而来,第三章开头的“忧心惸惸”亦来自第二章末句“忧心愈愈,是以有侮”,而此章开头“瞻彼中林”的目光,也显然源自上一章末句的“瞻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