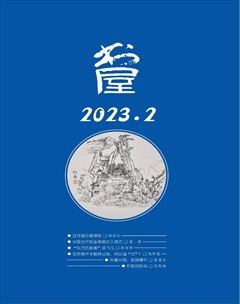朋友提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我说见过真迹。她问在哪儿,我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她说那是后半卷,我说是一整幅。她愈发惊讶。2011年,我随团去台湾旅游,机会很好,残画合璧,大陆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前半卷《剩山图》跨越时空来至台北,与后半卷《无用师卷》会合。
偌大的展厅,站在近千年枯黄的画作前,人是苍茫矮小的。那细远杳冥的情致韵味让人深陷其中,仿佛自己便是那个手持盲杖的古人,行于层叠曲折的旧山剩水之中,潸然洒泪。作者的平静孤寂、伤痛落寞盈然在目。一幅历经战火洪水、颠沛流离,被沈周、董其昌、吴之矩等无数人所藏之作,能存活下来,本是奇迹。
那种枯墨焦枝所延伸出的萧索意境,似幽暗炉火,烤手自暖的隐隐雪意。我甚至相信自己与他们是相通的,在迷茫的烟岚中,寻找着最平淡的言语对话。无须确认,总能于寂静松涛下小酌一杯,再默默离去。
千百年后,我在等它,且读懂它。
一
国画省笔,追求至简意境。往往一只飞鸟便代表一片天空,一叶扁舟代表一方水域。简而达意。宋朝的《双鸳图》,鸳鸯画至齐胸,两道波纹代表腹部淹没水中。画鸭子、鹭鸶没脚,亦属同一表达。绘瀑布往往只画出两条白线,中间空出即可,两旁是乌压压的群山。这种“以一当十”的手法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很常见。天水不着一笔,用纸张、丝绸的空白处代替,也算一种便利。
这种经济的表达也体现在戏剧上,舞台表演亦靠画面语言呈现。传统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萧恩父女,两个人物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晃动,意为船在颠簸。《三岔口》明亮舞台上的夜间打斗,靠摸索的动作显示黑暗的存在。演员扬鞭,在舞台哒哒哒转上一圈,即奔驰千里;双手一摇,驾舟远去。花轿一颠一颠,床一涌一涌,意思已然明显。简到不能再简,用动作代替环境、道具,毫不费力,追求意会,其手法与绘画如出一辙。
外国人求真求实,注重实景表达。所以西画满,不留空间,没“留白”一说。天是蓝的、灰的、黑的,用颜色填满,往往还飘上几朵白云或缀上几颗星辰,这在列维坦、梵高的画中均有体现。讲究情绪的饱满、透视、多维空间的叙述,而国画追求二维的平面语言。
尤其西方的古典画派画得极细腻,连贵妇人裙上的丝绸质感、珠宝光泽,皆毕肖。他们追求这种逼真效果,以肖像为主,反映法国贵妇优雅闲适的生活,属宫廷画、活人史,乃学院派产物,用古典手法表现现实场景,意在状物。而国画达意即可,追求精神内质。
一个空,一个满;一个简,一个繁;一个虚,一个实。
如《红楼梦》里的黛玉、宝钗的形象,黛玉空灵,宝钗充实;一个趋近于精神,一个忠诚于物质;一个神界,一个凡间。宝钗太过圆满,包括长相、处事风格,以及后来嫁给宝玉实现金玉良缘,而黛玉是惆怅凋敝的。
伯仲无须多言,空灵永远是现实版的升华。
二
绘画表达同样影响着文学的进展。中国古代文学同样追求诗化语言。所谓诗化,即美好化、精神化、理想化。这导致我们的诗歌特别发达,大批名家巨擘喷涌而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他们抒怀幽情,笼统含蓄,甚至无边想象。
西方追求视觉再现,故小说特别先进,走在世界前沿,用场景、对话于纸上推进。中国小说却尘封冰下,即便到了乾隆年间的《红楼梦》与清朝末年的《海上花列传》这样呕心沥血之作,作者都不愿署名或不署真实姓名。此做法非低调,也非不重版权,而是小说地位低下,囿于当时大环境、大思维,被正统排斥所致。
许渊冲先生在《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一书中提到杨振宁当时对中外诗歌的对比评价,认为外国诗歌太直白、太满,话都说尽了,没了余音。
这便是根源所在。我们古代国画的审美是半抽象的,苍山老水,花鸟鱼虫,大多在书斋完成。画者虽无数次观摩自然,但不重写生,偏重自我,所绘的鸟已非大自然的鸟,而是长着自己精神羽毛的鸟,也是全天下的鸟,更具艺术性、代表性。而西画讲究透视、素描、外部空间表达,更立体形象。所以,达·芬奇研究解剖学,且亲自解剖尸体。国画追求精神逼真,而西画崇尚技术逼真、状物的惟妙惟肖。
西画透视以人为原点,还原视觉原貌,属三维空间,毕加索又开创了四维表达。国画没有基本点,“俯仰皆得”,任意切入,山水层层打开,不受人眼所制。全视角、全方位,所述意象更为广阔。看似平面,实为真正的多维表达。
所以,东、西方绘画的立足点不同,一个以具体的人——画者所站位置为出发点;一个散视,以缥缈宇宙为出发点。
三
在绘画方面,我们老祖宗眼中是没物质属性的,即看不见具体物质,即便有,也是工具。表达的多是内心感受,往往是哲学的延伸。所以中国古人崇尚线条,用线条表达所绘之物。线条清晰明了,本是物体的提炼概括,又极具韵律感;而西画丰满厚实,用体积呈现。也可以说,中国人是“唯心”的,外国人是“唯物”的,这是他们的分野或倾向所在。
一个追求似是而非的意境,神似形不似,处似与不似之间;一个追求真实可感的场面,光色的變化。一个重内心环境,一个重物理环境。
早期西画主要为权势宗教服务,包括文艺复兴时的米开朗琪罗。所谓的文艺复兴,即把文艺归还给文艺,使之独立出来。
文艺复兴“美术三杰”: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达·芬奇画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是他心中的女神,那迷人柔意的微笑便是作者自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