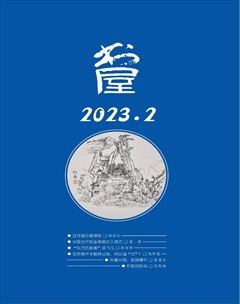六经失旨,百家裂道,诸子遂各执一端以为是。智、业歧途,导致儒、道分流;天、人对立,乃有杨、墨抗衡。孟子云:“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可见一斑。
从思想史的演变来看,侧重业分的儒家道德实践若未上升到对“性与天道”的觉悟,则终究难以超越功利世界升华到道德的自律与自觉,仁义圣智往往流为形式,成了小人求取利禄的敲门砖、大盗手中的窃国利器。道家对儒家的批判,所谓“绝仁弃义”“绝圣弃智”,正是从形而上之道的角度,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为最高境界,要求儒家放弃有我之执、功名之念,在天地境界上践履内圣外王之道。但从偏好智分的道家自身的立场来说,逍遥游式的即身解脱之境才是其终极归趣。“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应帝王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为之大用。另一方面,儒流变而至于荀学,弃天人之学于不顾,虚设礼乐以图富强,已为法家预作张本,其路数接近古印度六派哲学里徒重祭祀而不敬神明的弥曼差派。
墨家者流,《汉书·艺文志》云:“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清庙即明堂。周之明堂,即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乃祀五帝之所,为神教之府,凡宗庙、朝廷、天文、学校、官府一切功能,悉纳其中,为天地人一体共治之体系。顺四时而行,即《礼记·月令》所述之制。《月令》条举某时当行某政,非其时则不可行。苟能遵守其说,则政无不举,而亦无非时兴作之事,国事自可大治。《论语》记载,颜渊问为邦,孔子首告以行夏之时,精意实在于此。此诚治民要义,而古人之信守则由于敬畏上天。观《月令》所载,行令有误,则天降之异以示罚,其意可知。此等天神,皆有好恶喜怒,一与人同。若如其他诸子之说,所谓命者,于己于人,皆属前定,更无天神降鉴,以行其赏善罚恶之权,则明堂月令之说,为不可通矣,此墨子所以非之也。严父配天,事始于禹,而墨子法禹。《论语》载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体现出对祖先、神明祭祀的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起源,从发展机制上看,是由巫史通神灵,由祖神通天帝;从结果上来看,是从神权诞生王权,从祭祀发展成礼乐制度,夏正是中华文明的起点。是故墨家代表了华夏文明之根本所在。
墨家之学,以敬天兼爱为其根本。《天志》《明鬼》乃以鬼神世界威临人间,使世人生发畏敬之心,彼此兼相爱,交相利。《尚同》以天为极,即《尚书》之建立皇极。墨子所谓天、所谓鬼,皆具人格性,有喜怒欲恶,非如先秦诸家言天言鬼神,皆近泛神论、无神论。从吠陀体系来看,墨家虽不出业分之范围,但突出了巴克提或虔信的地位和作用,遂具有了教分的特质。故墨家尤重苦行,《庄子》论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尽管如此,墨家对人性的解说明显失于肤浅,虽提倡敬天兼爱,却大抵停留在世俗功利的层面,缺少超越性的精神维度,遂沦落为一种普罗大众的平均主义信仰,濡染了首陀罗的心理特质。是故墨学最终为上层精英所抛弃,反以各种变化的形式为民间的游侠、帮会所托命,并在民间起兵时发挥凝聚人心、号召牺牲的强大作用。
与墨家的集体主义和虔信精神不同,道家更关注个体生命的超脱和对宇宙演变规律之自然主义式把握。如果说儒家属于业分,墨家倾向教分,那么道家明显对应于智分。关于道家之学,《汉书·艺文志》云:“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实为道家最要之义,而皆指向对自我、天道之覺悟与修证。道家的修证路数跟古印度瑜伽术如出一辙。
华夏流传下来,明显接近瑜伽术,有文字、实物可考的是导引和行气。“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导引是长生术,结合了形体的屈伸俯仰和呼吸的吐纳出入。关于导引的方法,《庄子·刻意》篇云:“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之所好。”《后汉书》之《方术·华佗传》讲五禽戏:
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熊经,若熊之攀枝自悬也。”鸟申,意为像鸟飞而伸脚。鸱顾,《淮南子》里也有“鸱视虎顾”之类的名目,李贤注曰:“鸱顾,身不动而回顾也。”这几种动作都是瑜伽术里常用的体式。五禽戏为仿生导引,姿势的名称由动物名加其动作名而构成,与瑜伽体式的取象法则有共通之处。马王堆出土帛书《导引图》第四十九式为熊经,其他还有模仿龙、虎、猿、鹤、蛇等动作的姿势。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西汉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上有熊经图案,即模仿熊之动作。可见导引术之应用颇为广泛,且传承不绝。
行气之术,见于《庄子》《素问》《难经》等战国秦汉文献。最早讲行气之术的出土物是战国时期的《行气铭》。铭文经考古学家考释已可通读,全文如下:“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
李零先生释读为:“下吞吸气,使气积聚,气聚则延伸,延伸则下行,下行则稳定,稳定则牢固,牢固则萌发,萌发则生长,生长则返行,返行则通天。天的根在上(指下行),地的根在下(指上行),顺此程序则生,逆此程序则死。”
天根指上丹田,即泥丸;地根指下丹田,即脐下丹田。整个功法应属沿任、督二脉行气的小周天功。
按行气即瑜伽八支中的第二支——调息。《行气铭》所谓“固”“萌”“长”“退”应该属于调息中的悬息法,下行为内悬息,即吸气后蓄气不呼;上行为外悬息,即呼气后闭而不吸。下丹田对应于脐轮,是生命元气的中心;上丹田对应于梵穴轮。诃陀瑜伽认为,通过修持,体内的气沿着中脉逐渐上升,最终汇聚于头顶梵穴,到达这里,行者就超越了一切物质欲念,与梵相通。这应该就是《行气铭》所说的“通天”。
丹田之说与太一有关。丹田即神阙,对应于北极,而北极为太一之所居。汉桓帝延熹八年(165)边韶《老子铭》:“存想丹田,大一(按:即太一)紫房。”蔡邕《仙人王子乔碑》:“或弦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历丹丘(按,即丹田)。”这暗示养生并不是最高境界,觉证太一或通天才是行气的终极目标。所以庄子说导引养形,不过“为寿”而已。这种说法,通调息于太一,已经接近了瑜伽的第八支,即归依宇宙大我的三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