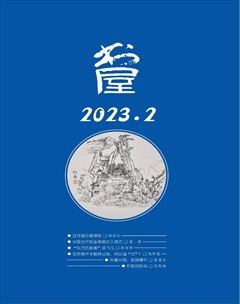主席先生:
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
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去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这是国际沙眼防治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gainst Trachoma)在1980年6月26日发给中国眼科学会的短函。要将这个曾让汤飞凡翘首以盼的好消息转达给本主,中国眼科学会其实是爱莫能助的,因为在拯救世人的眼上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汤飞凡早在1958年9月30日就已逝世了。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出现问题后,严重的话,人便堕入了黑暗,眼如是,心亦如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至少曾有六分之一的人因患上沙眼病而模糊了视线、黯淡了心情。沙眼病极为古老,一度有“埃及眼炎”之称,因为在人类可考的文字中,这一疾病最早是用古埃及象形文字记载下来。《黄帝内经》等中医典籍中记载的“粟疮”“椒疮”也就是沙眼。因感染沙眼后,患者的眼睑结膜表面会形成砂砾一样的外观,故有是名。
东、西方的早期典籍里都有为数不少的瞽、盲群体记载,有些典籍如《荷马史诗》就是盲人的作品,中国也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这些历史上的知名瞽叟,很多并非天生眼瞎,致使他们后天失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长期困扰人类的沙眼病。
沙眼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患者的眼部会分泌出大量的沙眼病原体导致视线模糊,患者为看清物象常需用手或布帛等擦拭眼部,沙眼病原体从而被转移,健康之人若是接触到被沙眼病原体污染过的手或物品,就很容易感染上。因此,往往某地出现了一个沙眼患者,在不久之后便会出现大批的沙眼患者。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国远征军千里奔袭,在金字塔之战中打败了曾在史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马穆鲁克骑兵,拿破仑因征服了埃及而扬名立万。然而,埃及这朵从沙漠里开出来的神秘璀璨之花也给拿破仑及其军队回赠了特殊的礼物——沙眼病。很多法国将士在埃及感染了沙眼,这一古老而活力四射的“埃及眼炎”随着凯旋之师登陆了欧洲,很快就在欧洲遍地开花。然后,又跟随欧洲人的探索与扩张步伐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美洲新大陆。1905年,美国国会甚至核准了一条新规,要求所有移民在进入美国之前,都需要接受沙眼检查。即便如此,沙眼还是在美洲泛滥起来,在印第安人集中的区域尤其严重。十九、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美国医疗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沙眼调查、防治、报道等资料。
由于人口众多,居住空间比较拥挤,中国人患沙眼病的情况较之世界大部分地区要更加严重。根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调查可知,城市里沙眼患病率大约在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而卫生条件较差、干燥缺水的边远农村患病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或以上,甚至有“十眼九沙”之说。在汤飞凡发现沙眼病原体之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沙眼平均发病率为百分之五十五,因沙眼致盲率高达百分之五。
正是因为这一现实情况,汤飞凡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将精力放在沙眼病的探究上。
由于抗生素、X射线、疫苗等在医学领域的发现与使用,现代医学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但是,沙眼的病因与传染源却长期未能查明,因此沙眼依旧是困扰着人类健康、导致失明的罪魁祸首。当时各国医学科学家关于沙眼病原体的学说主要有病毒、细菌与立克次体感染三种。尤其是日本细菌学家野口英世声称沙眼的病原体是一种颗粒杆菌,这一学说影响巨大,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推崇。然而,方向错了,越努力离目标便越远。科学家们按照这三种说法尤其是野口英世提供的方向对沙眼病原体进行了无数次探索与实验,但却始终无法解决沙眼病的问题。
汤飞凡与助手经过数百次细菌培养、实验,都无法证实病毒、细菌及立克次体感染与沙眼之间的直接联系。他也证实了颗粒杆菌并非沙眼的病原体。
可就在这时,日本侵华战争愈演愈烈,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南下,淞沪会战爆发,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汤飞凡在用自己的私财创建起来的细菌学实验室里再也无法安心工作,他的沙眼研究工作就此中断。他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随医疗队驻扎宝山,多次主动请缨前往第一线救护站救治伤员。救护站距离火线仅有几百米,完全处于日军炮火的覆盖之下,很多医护人员因此受伤。参加红十字会后勤支援工作的妻子担心他的安危,但在救护站见多了生死的他却安慰爱妻说:“你别怕,我个子小,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上海沦陷后,他放弃了跟随雷氏德研究所(自1932年起,汤飞凡兼任英国设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细菌系主任)撤到英国的机会,考虑到瘟疫往往與战争如影随形,他接受了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颜福庆的建议与邀请,在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中央防疫处始建于1919年,鉴于数年间东北三省和华北地区大规模鼠疫流行造成民众死亡惨烈,北洋政府借鉴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经验,在北京创办了由国家管理的专门防疫机构,负责防疫制品的研制、鉴定与使用。“九一八”事变后,中央防疫处迁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