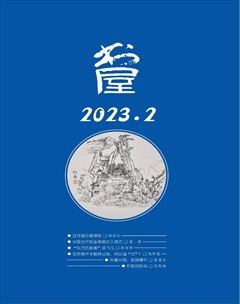一
“譬喻思维”是最近几十年来现代语言哲学家非常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语言哲学家主要以西方语文作为素材来研究、归纳、区分三种譬喻的类型:(1)实体譬喻,以具体实存之事物来譬喻抽象之义理;(2)空间方位譬喻,如用上、下、高、低、远、近、深、浅等方位进行譬喻,使具体、不具“价值涵义”的方位认知转化为抽象性的、具有道德意义的价值取向;(3)容器譬喻,以容器作为譬喻而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这三种类型的“譬喻思维”也常见于儒家与佛家经典之中。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也常以“类推思维”拉近“来源域”与“目标域”之距离,消除人对事物之陌生感。所谓“来源域”,是指譬喻所从出之领域中的事物,如“山”“水”等具体事物;所谓“目标域”,是指譬喻所指向之目标,如“仁”“智”等抽象价值理念。“类推思维”常见于儒家经典之中,如《孟子·尽心下》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但是,荀子却反对以譬喻作为辩说的方法,《荀子·非十二子》中说“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刘勰《文心雕龙》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刘勰认为“比兴”式的思维有助于拉近人与物的距离。中国文化中的“类推思维”或“譬喻思维”,常通过“比”与“兴”的思考方式而进行。
二
中西文化中均各有其源远流长的“譬喻思维”传统。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所著《诗学》中曾说:“隐喻字是屬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譬喻之运用习见于古希腊人之论著,亦习见于后来中西哲学传统之中,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曾提出,造成哲学家的荒谬结论的有六个原因,其中第六个原因就是“用隐喻、比喻或其他修辞学上的譬喻而不用正式的语词”,他认为譬喻之运用乃哲学思考不彰之原因,此说实属无稽之谈,难获学者之共许。
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类推思维”颇为发达。中国古代之“类推思维”方法,古籍或称为“辟”“援”,《墨子·小取》论所谓“辟”或“援”的思考方法说:“辟也者,举他﹝原作“也”,从王先谦改﹞物而以明之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
或称为“譬”,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以己之所欲譬之他人,就是为仁的方法。朱熹在与学生讨论孔子这句话时,解释“能近取譬”说:“如释氏说如标月指,月虽不在指上,亦欲随指见月,须恁地始得。”朱子以“随指见月”说明譬喻,出自《圆觉经》,颇能阐释譬喻之作用。西汉刘向《说苑》卷十一将“譬”解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譬”或称为“譬喻”,东汉王符《潜夫论·释难》云:“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礼记·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前引亚里士多德对Metaphor所下之定义,与《墨子·小取》“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刘向《说苑》“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潜夫论·释难》“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诸说若合符节,可以互相发明。
古代中国文化中常见的“类推思维”,起于古人对宇宙万物之分类,《周易·系辞下》说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中国古代文化中之“类推思维”,表现为中国文学中的“比”“兴”,而其“来源域”则多元多样,不一而足,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中国文化中的“类推思维”或“譬喻思维”,具体运作方式不一而足,或采“以偏例全”之思路,如《庄子·齐物论》之“罔两”与“景”;或以“天”喻“人”,如《逸周书·时训》以“蛰虫不振”喻“阴气奸阳”,以“鱼不上冰”喻“甲胄私藏”;或以“古”喻“今”,如儒家之历史思维;或以外在之事物喻内在之情感,如《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黛玉咏菊诗“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或以具体之事物喻抽象之本质,如以“山”喻沉稳厚重,以“水”喻流动不居,以“海”喻深不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