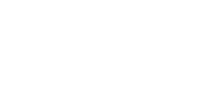通常以为秦汉以降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不外两种模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即做了官的;穷,即做不成官的。细按历史脉络,也不尽然。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的光谱,远不是穷、达两极可以涵盖的。这儿写的段玉裁、钱大昕、袁枚三人,或许能够说明这人生光谱也是穷达之外另有可能。
段玉裁:“所居西湖楼,一灯荧然”
传统中国社会的职业分类,大而化之来说是“士农工商”。“士”就是读书做官。后面的三类即务农、做工、经商。在近世大学或科学院没有成立之前,学者是靠什么职业来谋生而得以专心著述的呢?大概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做大官,比如乾嘉巨子阮元,江苏仪征人,大官僚,位高权重,身边有幕僚有学术班底给做助手;另一个途径是家里有点儿银子,衣食无忧,比如也是乾嘉巨子的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也做过大官,但主要是自己著述,没有幕僚班底来给查录资料或代笔。传说念孙在老家撰著《广雅疏证》,每天上午做三个字的注释,下午则泛舟高邮湖。这日子要是家无闲财,怎么过得了?这两个途径之外,要能够专心研究学问写论文写专著,可能就比较艰难了。比如段玉裁。
段玉裁是清代有大名的语言学家,他写的《说文解字注》一书,是可以辉耀古今的中国语言学巨著。但玉裁的日子过得是不宽裕的。
玉裁,字若膺,生于清雍正十三年,纪元1735年,江苏金坛人,也入过仕途,但做的都是县令这样的七品芝麻绿豆官,食少而事繁。玉裁25岁中举,但也就止步于此了,此后科举路上再没有进步。38岁后到四川先后做了富顺、南溪等地的代理县官。《光绪叙州府志》记玉裁“学问渊博,礼贤下士”。南溪今属四川宜宾,富顺今属四川自贡。南溪、富顺两县当时均属叙州府。抗战时中研院史语所迁到南溪的李庄,因此得以发现了不少玉裁做当地县令时的手批公牍。
玉裁做县官,政余则研经问学。玉裁后来在《书富顺县县志后》写道:“丙申二月,金酋平,民气和。……予乃能以其余闲成《诗经小学》《六书音韵表》,各若干卷。所居西湖楼,一灯荧然。夫人而指为县尹读书楼也。”
丙申年,即乾隆四十一年,纪元1776年。“金酋平”,即清军平定大小金川。玉裁这段话有两处可留意,一是说明玉裁治学在公务之余,而不是占用公务时间。二是当时玉裁在富顺县署之西湖楼秉烛研学,已成富顺一景矣,民皆知玉裁县尹挑灯夜读。玉裁勤于政事,公务之余也不是吃来喝去,而是专心问学。玉裁在自己写的《六书音韵表》卷首里也说过类似的话:说当时“王师申讨大小金川”,自己“无敢稍怠”,不敢耽误朝廷军机大事,公事处理完毕,“漏下三鼓”,才在灯下撰写修改《六书音韵表》,“以为常”,就是习以为常了。“漏下三鼓”,就是三更天,半夜十二点了。这也可以见得玉裁的用功了。
也是在这一年,玉裁开始撰著《说文解字读》。《说文解字读》是定稿本《说文解字注》的长编,即初稿,定稿本改名为《说文解字注》。
但这样案牍劳形,也不是个事,终究对学术著述有碍。玉裁在自己父亲71岁的时候,向上级表示,请给他回家奉养老父的机会。上级领导以没有这样的成例给驳了回来,大清王朝的官员组织制度不允许玉裁这样做。于是玉裁再以称病而退了休。这一年是乾隆四十五年,纪元1780年,玉裁45岁。
玉裁从此告别公务员生涯,回老家专心致志地做他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了,58岁这一年的秋天,举家迁居苏州阊门外下津桥。没有了职官的收入,玉裁也就主要靠教馆维持生活,即在公学私塾里教教书来换得银子。谋取教馆的工作,有时也不是容易的事。比如乾隆五十八年,玉裁59岁,托老友刘台拱谋书院的教职,没能成功。玉裁心情不好,加以外感风寒,用中医的说法就是“心脉虚”,稍稍用点儿功,晚上就失眠。65岁时写给刘台拱的信里说自己“抱病而多事。内人主持柴米之务者也,亦复病废,不能理事。一家三十口,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上有大年老人在堂。故近来宿食不宁,两目昏花,心源枯槁”。自己多病,夫人操持家务也劳累成疾,全家三十人要吃饭,年高老父还在,自己因此寝食不安,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所以辞去公职,家里又不富裕,也不是就能专意于学术的。这里面也要克服很多的困难。玉裁的定力也是很了不起的。
书写出来,要雕版刻印,没有大笔银子也是办不成的。玉裁70岁时,冬天写信给王念孙,说自己写《说文注》,阮元曾资助刻印了一卷,“数年以文章而兼通财之友,唯藉阮公一人。”“通财”,这儿的意思是朋友间互通财物,自然主要指的是阮元资助玉裁。玉裁在这封信里询问念孙能否给予帮助刻印几卷?玉裁72岁时,冬天在一封写给念孙的信里,感谢念孙惠赠“四十金”,作为刻书的经费,“此种高谊,不胜感泐。”嘉庆十八年,纪元1813年,玉裁79岁,这年冬天,玉裁弟子内阁学士徐颋、明经胡竹严力任刊刻之費,《说文解字注》定稿本终得完整刻印成书。从写成到刊刻,又过了五六年。如果没有得友人、弟子的鼎力相助,寒士玉裁写成了这部语言学巨著,也是不能够梓版面世的。
玉裁写《说文解字注》一书的过程里,可能也受到过一些“无知后进”的困扰。所以嘉庆十一年,四月初二,72岁的玉裁致王念孙的信里就有这样的话:“《说文注》近日可成。近来无知后进,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颈望之。”这意思是说,近来的一些“无知后进”非议我玉裁剽窃念孙您的学说,若没有您的序言,不足以彰明我的学术发现,所以我伸着头颈企盼您的大序。可知玉裁也曾为“无知后进”所困。幸而有念孙等学术同道巨子的相重力助,玉裁才得以克服千难万难,完成这一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巨著。王念孙为玉裁《说文解字注》作序云:“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无此作矣。”许慎《说文解字》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纪元100年,念孙说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许慎这部著作问世以来的1700年间所未曾有的。
前面说到的刘台拱,江苏宝应人,也是乾嘉学派的巨子,玉裁生前好多次在给台拱的信里,感激台拱给他的勉励,使他有信心写成《说文解字注》。比如嘉庆元年(1796)九月,玉裁致刘台拱的信里说:“《说文》一书,赖吾兄促成之。”嘉庆五年五月的信里对刘台拱说:“此书赖足下促之,功莫大焉。”
王国维弟子刘盼遂写的《(段玉裁)先生著述考略》说:玉裁《说文解字注》三十卷是由《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简练而成。刘盼遂先生的这个说法,也是从玉裁那儿来的,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定稿后,回过头来给的这个说法。我以前看到这一说法,也真是感佩玉裁能够这么痛下笔管删削自己的著作:从五百四十卷删减到三十卷。后来看到朱小健等先生校点出版的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说文解字读》,始知《说文解字读》没有分卷,而是以许慎《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部首来分,每一部首标为一“號”,共五百四十“號”,正式定稿时才分作三十卷。
玉裁42岁开始写《说文解字注》,到73岁才终于定稿。这中间常恐自己老贫病而完不成。嘉庆六年春天,玉裁大病,给王引之写信,说如果自己没能写成这书,请引之“踵完”,即请引之写完这书。引之是念孙的哲嗣,小玉裁三十余岁。不过好在这书终于在玉裁有生之年亲手写成了,真是幸事。又过了8年,嘉庆二十年,玉裁病逝。王念孙闻玉裁卒,谓人曰:“若膺死,天下遂无读书人矣。”念孙这个话,见于《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类别里的玉裁传。
在近代大学或科学院没有成立之前,像段玉裁这样以平民布衣靠教馆为生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真是千难万难。现在有了大学,有了研究院,可以既有薪金又能获得研究基金资助,真是应该感到庆幸了。有时看到有些拿了科研基金做项目,还要东抄抄西作假,胡乱整成一个东西交差了事,想想真是太不应该了。
玉裁是语言学大师,也是文理兼通的。玉裁尝扩展传统的《诗经》《尚书》《周礼》等十三部经书为廿一经,即把《大戴礼》《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八部大书与十三经合为廿一经。玉裁所欲增入的八部经典里的后面两部是数学著作。玉裁78岁时还说自己“近者闭户一室中,以廿一经及吾师《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恭安几上,手披口读。务欲训诂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见。不敢以老自懈”。文中所说“吾师”,即戴震戴东原。玉裁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了。玉裁是对学问真有兴趣,肯花费心力下功夫来写书的,而不是只为了谋个生计糊个口弄几文钱给自家花花。
附带说一下,玉裁与浙江尤其杭州也是因缘深厚。外孙龚自珍,杭州人。玉裁也曾多次来杭州讲学、优游,曾居西湖苏公祠。刘盼遂先生著《段玉裁先生年谱》记载,乾隆六十年(1795),玉裁61岁,这年九月,“杭州紫阳书院修葺完竣,杭之人士请先生作记,为作杭州紫阳书院碑文一篇。”紫阳书院在杭州城南紫阳山脚,光绪十八年(1892)改为仁和县高等小学堂。院址今为紫阳小学。可惜碑今已不存。玉裁的这篇碑文收在了玉裁《经韵楼集》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