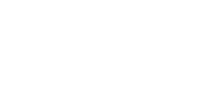一
我站在一块石头前。看它只是杵在那里,深灰色的岩身,竖直向下的纹理齐整排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似乎也没有。
一位叫做蓝晶石的地质学家嘱咐我来好好看看这块石头。
他说,位于神仙居南天门的这块石头,是白垩纪时期火山喷发后留下的古老遗迹,那么完整而高大的遗迹。
我们先来看一段关于白垩纪的描述吧:
“白垩纪是地质年代中中生代的最后一个纪,开始于1.45亿年前,结束于6600万年前,历经7900万年,是显生宙的最长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这块石头,它最老1.45亿岁,最年轻也有6600万岁。
伸出手,掌心贴近,冰冷、湿润、粗粝。
站在它的脚下,我想象它在遥远的白垩纪时代是什么样子。
蓝晶石说,这里曾是一座火山的喉咙。也就是说,在遥远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年代,滚烫的火红的岩浆从这里喷涌而出。浓稠的岩浆四溢,漫过大地。某一时刻,火山熄灭,世界冷凝,新的大地被塑造。将生命力平息下的火山口几经风化,剥蚀断裂,来到我们的眼前时,便剩下这样一副孤零零的顽固的面貌。
它真是苍老,我想。
雨中,白发苍苍的人撑着伞路过它的身侧,白鬓倏忽而过。对比起一亿年,人的苍老不过弹指一瞬。在这样久远的苍老面前,苍老已不是苍老,苍老即成为永恒。在永恒面前,人类多么渺小。在人类面前,它巍峨不语。而我看着它,同样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现在,这块石头拥有着年轻而现代的名字,它叫擎天柱。名字好威风,却鲜少有人细细打量它,神仙居更好看更巍峨的山石多了去了,更多的人,来了神仙居,便兴冲冲往山中去,去看西罨慈帆、画屏烟云、佛海梵音……观音、如来、风帆,在神仙居,美已被概括,已被公认。
像擎天柱这样的石头,与美的最小公约数还有一定的距離。人们陶醉在神仙居公认的美中,无暇过问这曾经炽烈燃烧的火山口的一点冰凉遗迹。
看吧,有人停下脚步来看我,他们再看看石头,他们一定疑惑,她在看什么啊?她为什么杵在一块石头面前不动?她为什么不上山?山上才有好风景啊!
总不好说,我试图看到它身上曾发生的一切。
二
得从1.5亿年前说起。
那时候,江南还远。
1.5亿年前,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地球正自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造山活动。这个时期为侏罗纪至白垩纪的过渡时期,许多地区地壳因受到强有力的挤压,褶皱隆起,成为绵亘的山脉。以北京燕山为典型代表,地质学家将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强烈的地壳运动称为燕山运动。
以下为关于燕山运动的描述:
“这时候,长江形成了,在长江的上游,形成了唐古拉山脉。在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以西,形成相对稳定的大型内陆盆地,在中生代期间已经连续地接受河、湖的沉积。盆地外围,固结了的古生代地槽带普遍发生基底褶皱,造成许多平行斜列的褶皱断裂山地与大量小型断陷盆地,并伴以岩浆活动。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花岗岩侵入和火山岩的喷发尤为剧烈,显示了太平洋沿岸地带构造活动的加强。”
我们大约可以窥得当时的一点景象,在1.5亿年前,燕山运动奠定了中国大地构造的地貌轮廓。而在脚下的浙江沿海一带,地壳活动频繁,大小火山正肆意喷涌,岩浆像红色的动脉输送热汩汩的能量,它们不知疲倦,向空中喷出烟云朵朵,直至某一刻,世界平息,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火山流纹岩地貌集群”。
我踩上一片山崖的一角,试图眺望远处云雾弥漫的山谷。伙伴怡妮指着它说,这是一块典型的流纹岩。和门口的擎天柱不同,这是一块山石,它从山路向外延伸,供人行走到山崖的边缘看风景。
下了雨,流纹岩被淋湿,显得乌黑、凹凸不平。隆起的部分水润润光溜溜的,显然,数不清的脚步从它身上踏过。如果不是怡妮的教导,我们甚至都不会看它一眼。如果不是怡妮的教导,我们也只好说它是一块石头。
怡妮在神仙居做资深向导,流纹岩地貌是她常对人提及的对这座山的定义。她还知道,流纹岩构成了神仙居奇绝的地貌。我们笑,你的工作就是给来神仙居的人介绍石头。她转身指着一株树身上的白色斑块说:“不仅仅是,我还介绍空气,这是氧斑,代表着这里含氧浓度高。”
我们深吸了几口。
雨天的神仙居,被云雾笼罩。我们吸入肺部的,仿佛是雾、是云,吐出来的,仿佛也是雾、也是云。空气清凉,沁人心脾。云雾遮盖住浓稠的绿色,绿色的树,绿色的山,全都消失不见,只有云雾泛青,青色透出古意。
这样氤氲水汽弥散的天气,上神仙居的人就少了。上了山的人,脚步也慢了。看吧,不远处,一个山顶的亭子下,一个人侧身静静坐着。云雾将他笼罩得只剩一个单薄的深灰色的剪影。山崖下的栈道上,一个穿着荧光服的男人,正慢悠悠踱步向前走,那是神仙居的巡逻队员。他们分别游走在一座山的山顶与山腰,而我们呢,站在山的另一侧,悄悄看他们。
山上多么静谧啊,静谧得可以听见雨滴从叶尖滴落的声响。脚步声被岩石吞没,而指尖暴露在空气中,仿佛窸窣的水流从体内沿着指尖滴落下来。这样的雨中山,人体内的声响胜过山本身的声响。
我们站在云中,等待一片“风帆”的出现。古老的火山石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令人充满遐思。云雾笼罩的“风帆”,仿佛通往仙山的海上——在以神仙命名主题的这座山中,我们不由自主地脱离现实。大地静止,只有云雾在极其缓慢地腾挪。
噢,不对,我想起了地质学家蓝晶石说过的话——大地从来不会静止。喜马拉雅现在平均每年上升一厘米,直布罗陀海峡也在逐渐缩小,直至某一天,它会完全消失。
“大地时时刻刻在运动。只是,不在人类历史的尺度之内。”
大地有它构造的自我意志。我们所能看到的,也许是某一阶段构造的一个结果。神仙居是地球经过火山喷发、地壳抬升、断裂切割、崩落垮坍、风化剥蚀的一个结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沧海桑田的过程。
在这样漫长的过程中,人类还未形成呢,但是,像神仙居这样的风帆、如来、蝌蚪文,却早早出现。第一个发现它似乎存在和人类某种联结的人,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心情呢?
我询问一位山脚下的“山民”:“你什么时候见过神仙居的山?”
她在山下开一家小餐馆,世世代代为仙居人,她说:“老早就有的呀。”
在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风景,产生于人类有记忆之前。只有像蓝晶石这样的地质学家,才能明确分清大地、时间、记忆的先后。在自然面前,记忆是最苍老的,却也是最年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