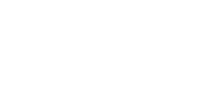一
小时候,我跟随父母亲生活在甘肃平凉,一直到17岁高中毕业参军离开。幼年、童年、少年时光的事情至今印象深刻。
这天中午,有学者在《百家讲坛》讲述“穿越千年的夯土”时说到了“胡墼”。近50年没听过这个词,我的记忆猛然被激活了。
所谓“胡墼”,估计许多人不知为何物,不识“墼”这个字。尤其在江南地区,知道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说文解字》的解释曲里拐弯:“墼,令适也,一曰未烧者”。“令适”就是“令甓”。“甓”就是砖,墼就是未烧的砖;《汉语大辞典》的解释简单粗暴,“胡墼:方言,土坯。”《新华字典》的解释不很准确:“墼,未烧的砖坯。粉末加水做成的块状物。”看来用以规范文字的字典也会出错:胡墼不是砖坯,亦非“加水的粉末”。
胡墼(jī)其实就是用黄土夯打而成的土坯,是一种取材广泛、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生态环保、经济实惠的建筑材料。胡墼也称胡基、胡期、胡其、土墼。胡墼是长方形的。大小我说不准。大体是四块标准砖头合起来的尺寸,厚度约10厘米。也许更大些。作为黄土高原常用的建筑构件,胡墼的用途非常之广泛:盖房、砌墙、盘炕、垒圈、搭棚、箍窑。经济实惠,冬暖夏凉,特受老百姓尤其是穷人的欢迎。大西北那些千年古刹、古老宫墙、牌楼院墙、百姓老宅,到处能看到胡墼的身影。
作为极其普通和大众化的建筑材料,胡墼对人们的生存繁衍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它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赠,作为中国北方文明的开端,惠泽一方百姓,是人与自然共同创作的奇迹,黄河文明的优秀篇章,黄土文化的杰出典范。
二
我对“胡墼”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或曰“胡墼情结”。这种敏感的体验来自一段古城墙根下生活的经历。
从小到大,我家都住在平凉市人民银行家属院。这个很大很空旷的院子,位于城区东大街南侧的“九天庙巷”与“南极巷”拐弯处。大院住着20多户人家,都是银行职员和家属,当时银行的职员称作“银行干部”。院里家家户户分有一块地,种点玉米、向日葵等。我家还种了党参、烟叶、黄花菜。没事的时候,我也经常和弟弟妹妹在地里忙活忙活,每年都小有收成。
出大院门楼右拐百米,有段不算很残破的长城,我们叫它“城墙”。甘肃人把城墙的计量单位叫“堵”,城墙用黄土夯制,没有包砖。估计至少是汉代修筑的。城墙的高度大约有20米,另一边是广阔的低洼地,与我们这边的高差有十多米,称为“南河道”。站在城墙顶看南河道,视野开阔,很远的地方一览无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刚好碰上十年动乱和“复课闹革命”,功课不紧张,没有“家庭作业”这一说。参加“红小兵”“红卫兵”也没什么活动,放学了就成群结队去踢足球,瞒着老师和家长去柳湖游泳。回家后或去井里挑两担水灌自家水缸,或到父母单位去打两三瓶开水,或者帮忙拉拉风箱。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能不受限制地尽情玩耍。经常和院里年纪相仿的一伙人纠集起来爬城墙。顺着城墙上的脚窝,脚蹬手攀爬上去。
城墙顶部不是很宽,没有垛口。每隔百把米就有一个人工竖井。想来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炼钢铁”时挖的炼铁炉烟囱。洞壁两侧挖有从上至下的脚窝,我经常踩着脚窝沿洞顶爬至三分之二处,因为下面是二十到三十多平方米圆形的炼铁炉,下不去了。大炉子和烟囱壁呈“火烧土”样,纯净的黄土长时间被火烧过,呈发红发黑疙疙瘩瘩的琉璃状。有时大家也成排坐在城墙边缘,看着南河道的景色,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无聊的话或者发呆。
城墙根有个比足球场大点的土坑,可能是当年修长城取土留下来的,我们称“垃圾坑”,一直是附近老百姓倒垃圾的地方。积年的垃圾只占了大坑很小的一角,剩下很多地方成为胡墼制作场。少时有一组人、多时有三五组人在打胡墼。每组多则2人,1人供土,1人捶打;少则1人,自供自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