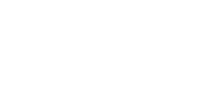6.跳蹿蹿
《红楼梦》的宏观架构固然巧妙而自然,草蛇灰线,千里伏脉,一切尽在掌握中。而曹雪芹的细部功夫则造就了这部伟大小说的结晶般的叙述质地。精彩细节,星罗棋布,静读细想,回味无穷。
来欣赏第六回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语言细节。
家境不堪,冬事难办,刘姥姥硬着头皮鼓起勇气,借连过宗的由头,决计亲自到荣府走动一次,指望着能在荣国府“拔一根寒毛”以救急度日。
刘姥姥原是一个有生活历练与乡野智慧的农村老妪,她的心态也放得平正,至少没有孤注一掷患得患失,这就很难得,也是她最终不虚此行取得成功的关键:
“倒还是舍着我这付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
但毕竟是初次来到公府侯门,曹雪芹必须写出豪门的气派与刘姥姥的忐忑拘谨之态:
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簇簇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蹭到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
簇簇轿马如画,掸衣服如画;蹭字极准确,更准确的是只蹭到角门而不是大门。而挺胸叠肚、指手画脚、说东谈西三个词,写尽天下豪门仗势欺人狐假虎威的家丁与仆役。
众人问蹭上前来的刘姥姥:
“那里来的?”
刘姥姥陪笑着答非所问: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烦那位太爷替我请他老出来。”
不接茬,超逻辑,生活中的人不就是这么说话的么。当然,以刘姥姥的人生经验与智慧,也自然明白没必要细说自己从何而来,说了肯定不如不说,而家丁们只是没话找话摆虚架子罢了,并不真的关心她从哪里来。所以,她就跳过这茬直接说出了自己来此的目的或诉求。
众家丁“都不瞅睬”,过了“半日”,才让刘姥姥在墙角下等着。还好有一个老年人(一般都会有这样一个厚道老人,就像灰堆里总是隐埋着一丝火种),不忍心见刘姥姥被捉弄和调排,告诉她周大爷到南边去了,让她绕到后街上后门去找周瑞家的。
刘姥姥于是绕到了后门,只见门前有一些生意担子与摊贩,还有“闹吵吵”三二十个小孩在那里厮闹玩耍。刘姥姥便拉住一个孩子打听周瑞家的:
孩子道:“这个容易,你跟我来。”说着,跳蹿蹿的引着刘姥姥进了后门,至一院墙边,指与刘姥姥道:“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娘,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我带了来了。”
一个活泼的爱在外人跟前刷存在感的孩子,鲜活如画,栩栩如生。尤其是“跳蹿蹿”三字,如蒙太奇特写镜头般捕捉了这个孩子的肢体语言,摹写和塑造了魅力恒久的独属于孩子的生命造型与身姿动态:随着双脚极有节奏地一下一下交替蹬踏踮地,整个人像小火箭似的一蹿一蹿,不断踮地不断跃起,大地仿佛充满弹性,孩子就像踩着弹簧,那么欢快,那么自然,那么有活力。阅读时,这个人来疯的跳蹿蹿的孩子仿佛穿越了三百多年时空一下子跳到了我们眼前,并让我们瞬间回到童年的相似情景。
巴尔扎克在《乡村医生》的开头也叙述过类似的情景。上尉骑马到山谷小镇寻找倍纳西医生,榆树下集合着一群孩子,上尉向他们打听医生的屋子,也是有这么一个孩子主动来到了上尉跟前:
于是,这一群孩子中最不怕生、最爱笑、眼睛灵活的一个小鬼,赤着一双满是泥污的脚,依照孩子的习惯,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
“倍纳西先生的屋子吗,先生?”
他还加了一句:
“我领你去。”
他走在马儿前面,一则出于这样的想法:和一个陌生人走在一起,可以显显他的威风;二则出于他的儿童的殷勤,或者由于他急切需要活动一下,像他那样的年纪,精神上和肉体上时刻都有这样的需要的。
两个孩子何其相似乃尔!
曹雪芹与巴尔扎克仿佛心有灵犀。
7.刘姥姥的鼻子与浑身发痒
刘姥姥第一次来到荣国府,好不容易在周瑞家的帮助下,进入荣府的深宅大院,来到凤姐的堂屋:
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云端里一般。满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使人头悬目眩。
刘姥姥从没进过这样的豪宅大屋,心理的紧张自不待言,堂屋里的一切陌生而耀眼,所以一双眼睛根本不好使,视觉系统处于晕眩状态,虽然睁着双眼,却视而未见,莫衷一是。曹雪芹用了“满屋中之物”,说明刘姥姥并没看见任何具体的东西,在她眼前闪耀的只是满屋的概念性的物。
一个人突然来到陌异的晃眼的环境,他的眼睛的确容易晕眩,他的视觉容易坍塌失灵,但他的鼻子却并不会受到影响,依然功能正常,鼻孔照常张开,嗅觉照常运转。所以,曹雪芹叙述刘姥姥进入堂屋时,先写的是她的嗅觉:“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虽然“竟不辨是何气味”,那是因为那气味很陌生,她闻所未闻,而并非嗅觉失灵鼻子不好使。
这段叙述,一方面极准确地表现了刘姥姥的身心状态,另一方面,又极生动地展现了荣府之奢华之堂皇。真可谓一箭双雕,相得益彰。
到这一回回末,凤姐先说“大有大的艰难去处”,随后又答应把准备给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送给刘姥姥:
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
这一定是刘姥姥生命经历中的重大瞬间,从惶恐到狂喜,从地狱之黑暗到天堂之明亮,曹雪芹只用了一两句白描,便把这样的生命跌宕写得活灵活现,准确到了骨子底里。
为什么会喜得浑身发痒起来呢?因为刚刚还“心里突突的”,心脏悸动异常,血液凝固般停止了流动,忽然又听说可以得到二十两(那几乎是贾府大丫头两年的份子钱,对刘姥姥来说是多大的一笔巨款),心臟的压力瞬间释放,血液哗一下奔涌到全身,仿佛要冲出血管,淌到皮肤外面来,浑身岂能不发痒起来?!
轻描淡写,精确之极。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叙述水准。
8.送宫花或者散淡文本
一般的小说都是故事性的紧凑文本,而《红楼梦》则是生活化的散淡文本。
《红楼梦》的叙事,遵循的不是故事的逻辑,而是生活的逻辑。
具体而言,曹雪芹创构了一个《红楼》世界,万物各安其位,有楼有园,有鱼有鸟,有芭蕉,有海棠,还有苔藓,里边有众多男女人物,他们不是要演绎一个有教益有结构的故事,而像是在那个世界里呼吸和生活(就如拉夫·迪亚兹固定超长镜头里的演员,他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
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都不一定有什么逻辑和理由,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而没有理由往往是世界的理由,没有意义恰恰是生活的意义。
你看第七回开头,刘姥姥走后,周瑞家的要回王夫人话。王夫人却不在上房,问丫鬟们,方知往薛姨妈那边闲话去了。读到后面我们知道,王夫人到薛姨妈那儿真的没什么事情没什么理由,真的只是说了些家务人情的闲话,既不是铺垫也不算伏笔。
周瑞家的听说,便转出东角门至东院,往梨香院来。
如果是故事性的紧凑文本,大概只写“周瑞家的听说,便往梨香院来”,这样写完全满足情节所需,叙事既紧凑又有效率。但曹雪芹却叙述了周瑞家的是怎么走到梨香院的:“便转出东角门至东院。”
虽然周瑞家的不算是多么重要的人物,“转出东角门至东院”这个细节,对故事情节也并没有什么作用与意义,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没有意义的散淡的细节,呈现了人与时空的具象关系,呈现了生活的质感与真切,并营造了小说的空间感与现实感:荣府多大的一个地方,周瑞家的不可能从上房飞到梨香院,她必须一步一步转出东角门走到东院去。
周瑞家的到了梨香院:
刚至院门前,只见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儿,和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儿站在台阶上玩。见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话回,因向内努嘴儿。
周瑞家的要找王夫人,但曹雪芹偏偏先写在院门前玩的金钏儿和另一个小女孩。除了着力表现太太小姐这样的主要人物,《红楼梦》也从不忽视丫鬟嬷嬷这样的次要人物,给予我们的是人世纷纭众生同在的印象,就像在生活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