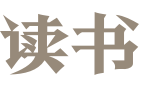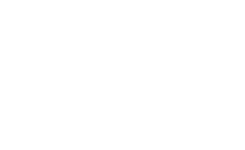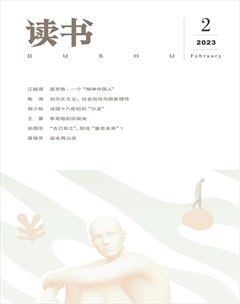公元一五八0年(明万历八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继葡萄牙王位,成为两国共主。对于姻亲、教派和政治关系复杂的欧洲皇室而言,这次王位更迭稀松平常,但却对全球版图有着深远影响。按照教皇主持签订的条约,大航海发现的新世界一分为二,葡萄牙掌控绕好望角东行的东印度航线,西班牙掌管横穿麦哲伦海峡西行的西印度航线。如今,随着西葡两国合归一主,两条最为重要的世界贸易通路最终会师澳门:一路由澳门向东,穿马六甲海峡,远航里斯本,另一路西进马尼拉,横渡太平洋,直达墨西哥的阿尔普尔科港口。值此之际,新的海上势力也在跃跃欲试:就在同年,亦商亦盗的英国探险家弗朗西斯·德雷克完成了环球航行;三年后,荷兰人林希霍腾远航至亚洲,绘制了著名的中国海图。一场欧洲海国的角力图穷匕见,即将改变四百年来亚细亚的命运。
虽则取材于如此雄奇壮阔的历史画卷,罗伯特·马克利的著作《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却未津津乐道于欧洲新老帝国的霸业,而是另辟蹊径,掀起“帝国的新衣”,显出其光鲜的历史叙事下藏掖着的“小”来。马克利反复强调的是,方今吾辈凭着历史的后见之明,往往以十九世纪末英帝国的巅峰之势来逆测十七和十八世纪初期欧亚交往的情形,认为英帝国可以凭借其先进技术、强大的皇家海军和庞大的贸易网络,“控制、重构和统御”东方(萨义德语)。马克利指出,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拥护帝国“文明”事业的殖民主义者,还是批判帝国压迫的后殖民主义者,都接受了“欧洲中心论”的前提:欧洲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全面统治着远东。
借助“ 加州学派”非欧洲中心的经济史叙事,马克利修正了萨义德提出的欧亚权力关系论述。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初的早期现代世界,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仍然占据着自然资源、财富、军事和技术优势,主导着全球贸易。因此,这一时期英国对远东的想象并不同于十九世纪极具侵略性的殖民话语,而是充满了对远东财富和权力的追慕和忧惧,甚至常常用“精神胜利法”的论调来粉饰和遮蔽其失败。与萨义德强调的欧洲主宰、压迫式东方主义不同,马克利展现的是羽翼未丰的英帝国如何在与亚洲强国的贸易、外交、传教和文化交流中遇挫,勾勒分析了一种“脆弱”的东方主义。由此出发,马克利志在书写一部“亚洲主宰时代的英国文学史”。全书涵盖两百余种文史材料,以英国经典作家关于远东的叙述为主线,爬梳同时代游记、书信、海图、地理志和贸易论,剖析英国社会对亚洲强国畏慕并存的微妙心态,力图改写欧洲中心的历史叙事。
一言以蔽之,本书勾勒了一部早期英帝國的“失败史”。十七至十八世纪初的英国尚未成为以“炮舰外交”横扫世界的“日不落”霸主,仍是远东竞逐中的边缘人,眼睁睁看着天主教的葡萄牙与没有“君父”的“暴发户”荷兰,先后主导香料贸易。彼时的英格兰仍是人口和资源有限的岛国,尚未大规模开疆拓土,皇家海军虽在十七世纪末开始称霸,但数量有限,不足以远征海外,配合欧洲以外的商业和殖民扩张。至十八世纪末,英国陆军的火枪、大炮和弹药的开支尚未逾总预算的百分之五。直到二十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租界的治安和武备仍主要依靠印度锡克族雇佣军。一八一0年,尚未击败拿破仑一战成名的威灵顿公爵慨叹道,囿于自身岛国的资源瓶颈,英帝国犹如“种在花盆里的橡树”。
一
面对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诸国的远东,英国及欧陆诸国的身份(或曰“文化自信”)受到重创。在贸易上,英国信奉的“自由贸易”在东亚的朝贡体系中寸步难行,无法挤进香料贸易,在葡、荷和当地邦国的夹击中沦为海盗;在文化上,中国完备详尽的古代史传体系撼动了《旧约》编年史的至高权威,来华耶稣会士和定居开封的犹太人后代,在礼仪、习俗方面逐步被儒家文明同化;在外交上,欧洲使节被中国和日本视为藩属遣来的贡使,沦落到廷前献艺的地步。
于是,面对远东的诱惑和威势,无论是位居帝国前哨的商人、使臣和外交官,还是凭游记、书信和地理志想象异域的文人,逐渐演绎出一套叙事策略,修正和掩饰英帝国的挫败,维系英帝国必胜的叙事和自我认同。马克利著作的主线,正是通过文本和历史的对勘,找到英国远东叙事中的“花招”,亮出其话语层面的“破绽”,展现了帝国复杂和脆弱的一面。
首先,英国并没有运用如今我们熟悉的东方主义式二元对立话语,划定文明西方和落后东方的分野,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三角关系”叙事—英国和香料群岛诸国联手对抗西、葡、荷等国的入侵和殖民。一六0一年,在成立不久的英属东印度公司资助下,英国冒险家兰开斯特携着伊丽莎白女王致香料产国亚齐的苏丹的信件。信中,女王敬称苏丹为“爱兄”,有意淡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异,凸显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以树立共同敌人来拉拢苏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