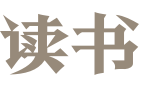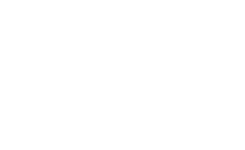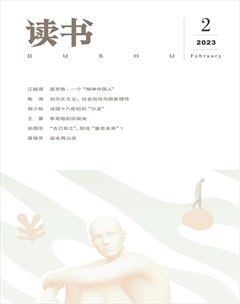邓正来先生离世后,在同其家属一起清理他的书籍时,我有幸获赠一本赵汀阳题赠邓正来的论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在这本书中,邓正来做了密密麻麻的阅读批注。赵汀阳题赠的时间显示,该书是二00五年七月送给邓正来的。彼时,邓正来已完成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文稿,并已在《政法论坛》上连载发表了这篇长文,正在为出版成书做最后的定稿工作。而其批注内容显示,他读完赵汀阳的这本书后拟对原稿的“引论”“结论”进行修改,同时要重新组织新增“自序”的问题建构。邓正来对赵汀阳天下体系理论做了哪些评价?他对《天下体系》的阅读,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成书修改?这是萦绕在我心间的两个疑问。在邓正来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见鞍思马,感慨尤多,遂成此文,以辨疑解惑,并為阅读和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添加一份学术史资料。
一
在《天下体系》第2 页,邓正来用下划线标出了这样几句话:“今天的这个世界共同运动和共同生活画面就是全球化。……今天中国正在重新成为大国决不是重温古代模式的大国之梦,而是进入一种新的政治经验。……经济的重量决定了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重量,经济的问题带动了政治、文化和思想的问题。”同时,他在旁边写下了“不妥!”(凡是邓正来的批注均以楷体显示,下同)和“经济决定论”。显然,他对赵汀阳此处洋溢着的“经济决定论”心存疑虑。
在第6 页,赵汀阳认为“真理必须是好的3 3,真理必须负责任,因为人类最终需要的是生活而不是真理”(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对应于邓正来下划的带圈着重号;下同)。邓正来不仅在这里加了着重号,而且在旁边写上了“好的生活”。可见,他对赵汀阳的这一论述深有共鸣。正如我们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看到的,他把这种“好的生活”进一步解读为“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并认为法律“要为中国人共享一种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服务”。
在第7—8 页,邓正来对赵汀阳关于中国思想的完整性或整体性的论述提出了疑问。他特意标出了这样几句话(下引括号里的文字是邓正来没有用下划线标出的内容,下同):“中国现在不再缺乏西方的各种观念,(所缺乏的是自己的)大局思维和整体理念。”“中国思想的基本特色就是它的完整性,其中的每一种思想都在中国思想的整体效果中才获得意义。”“中国思想只有一个系统,思想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正是中国思想的突出优势,(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表达完整的中国思维,)就是个根本性的失败。”邓正来在这三句话旁边,都标注了“为什么?”以表示自己的疑问。他之所以产生疑问,除了可能对传统中国的圜道—整体性思维感觉陌生以外,主要是对赵汀阳在当下呼吁这种“大局思维和整体理念”心生警觉。考虑到邓正来在知识论上对哈耶克“分立的个人知识”和“默会知识观”的服膺,他对这种整体性思维的警觉几乎是本能的、条件反射性的。
在第14—15 页,赵汀阳认为,“西方思想的底牌3 3”是把“主观性所‘化’不进来的东西”承认为“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这种绝对逃逸在外而绝对异质的东西只有两种3 3”:上帝和作为异教徒的他人。他同时认为,从个人主义、异教徒到丛林假定以及民族/ 国家的国际政治理论等陷世界于冲突和混乱的观念,都与承认超越者概念有关。对这一论述,邓正来在旁边写上了“是真的吗?”赵汀阳接着指出:“中国的思想假定的是,对于任何他者,都存在着某种方法能够将它化为和谐的存在;或者说,任何不和的关系都可以化成和谐的关系,任何在外的存在都是可以‘化’的对象而决不是要征服的对象。”邓正来在这一整句话旁边写上了“什么假定为依据?”。他的这两个疑问,一方面质疑了赵汀阳对“西方思想底牌”的论述,另一方面质疑了其关于中国“思想无外”这一文化特质的论断,特别是其有观点、无论证的论说方式。
在第17 页关于分析框架和方法论的论述中,邓正来不仅在相关段落画上三个“?”,而且将该页右上角折了起来,可见他对该页论述的疑问是较为集中的。从这三个问号对应的文字来看,他主要对赵汀阳的三个论断有疑问:一是“(西方政治哲学框架中)缺乏世界政治制度的位置”;二是“(由于缺乏更高的理想和视野,国际理论的背后根本不存在)任何深刻的哲学”;三是“(康德……试图创造的作为国际理论基础的国际政治哲学毕竟)与世界政治哲学(有着)难以跨越的距离”。这三个疑问,共同指向了赵汀阳关于“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以及他对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缺乏“深刻哲学”的批评。这些疑问可能意味着,邓正来对赵汀阳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除了天下理论,没有世界政治理论”的自雄倾向心生疑虑。
在第19 页,赵汀阳写道:“(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充满整个可能的政治空间的普遍有效性(和通达每个)可能的政治层次3 3 3 3的完全传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