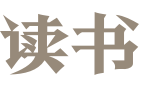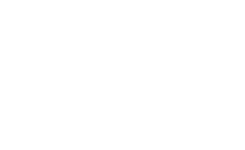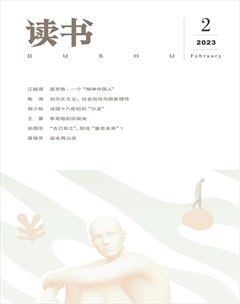《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一段音樂家与听众互动的精彩描述:“克利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在这个场景里,不动声色的听众给音乐家施加了无形且难以抗拒的压力。在审美的过程中,听众从来都不只是被动的接收者。欧洲美术史上, 历史画、肖像画、风景画的兴替都是听众的审美偏好所致;中国文学史上,从五言诗到七言诗到词、曲、小说,文学形式的演变也是由听众的习惯、喜好决定。
听众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中不被强调但又不可或缺的一方。公元一四00年,如果围攻济南城的不是朱棣的军队,当时负责守卫的山东参政铁铉就是拿出再多朱元璋画像,写下再多朱元璋神主灵牌, 堆满所有城墙垛口,恐怕也无济于事。从音乐、美术到政治、军事,在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不论听众在不在场,他们都是事件走向的决定者。如何认识、对待听众的力量是解读人类思想史的重要视角。
古典时期,早慧的希腊人高度重视听众的力量。希腊人看到了听众在思想交流中的主导作用,悉心整理出一系列以听众为中心展开沟通的演说经验,是为修辞学。修辞学能成为古希腊的三艺、七艺之一,根本上是因为言说在古希腊的公共生活中有决定作用。掌握修辞技艺,才能在公共交往中赢得听众认同,由之获得参与、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与这一作用机制相辅相成的是希腊人的语言观、真理观、民主制。古希腊人认为真理寓居语言之中(洪涛:《逻各斯与空间》),言语能力就是探索、发现、表达真理的能力。听众常常是不说话的与谈人,在探索、发现、表达真理的过程中,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与言说者互动。表面看来,是演说家在煽动、操控听众, 实则是听众,至少是演说家头脑中预先构想的听众在引导演说家说出听众想听的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林肯对这个观点做过恰当的限定,“在民主国家,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古人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在表达相近的观点。
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通过修辞学把听众的力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塞罗从修辞的角度解读人类社会的起源。在他看来,人们本来散居各地, 各自为阵、相互争斗,后来在某位演说家的号召下,才渐渐凝心聚力,组成最初的社会。西塞罗从政治、社会、伦理等多个角度思考过修辞学的相关问题,这些思考在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中得到体系化的表述。这部十二卷本的皇皇巨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修辞学涉及的各个层次的问题,在应然层面充分肯定听众力量的正当性,在实然层面系统总结调动听众力量的方法。
从罗马帝国后期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帝制确立、神学一统天下,听众的力量首先随着民主制一道式微。真理掌握在上帝、君主的手中,听众不是真理的共同发现者, 只是信息的接收者。修辞学开始与哲学分离,与真理的认识、发现无关。中世纪的人们一般从工具的角度看待修辞学,看重修辞学在布道时的作用,如查理曼大帝认为修辞学能够帮助他的子民更好地理解、接收上帝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