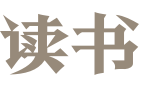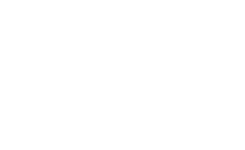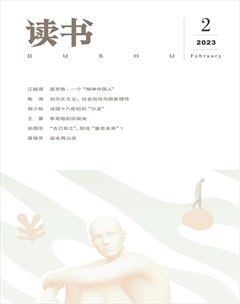从丹东开往北京的快车眼看就要到锦州车站了。这个时候正是过半夜一点多钟,车厢里的旅客随着列车有节奏的振动—哐哐哐,哐哐哐……—差不多都睡了。在六号车厢从里数第三个座靠外边有位老大娘坐那儿还没睡,这位大娘有六十多岁年纪,穿着青色的上衣、蓝色的裤子,脚下是青鞋白袜子。
这是评书艺术家田连元的成名作《追车回电》的开头。在一九六五年辽宁省“说新唱新”曲艺大会演上,二十四岁的田连元凭借自己创作的《追车回电》脱颖而出,录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文稿发表于《辽宁日报》(更接近录音的另一文字版本后来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曲艺集》,本文引述的是录音版),不仅开启了一个年轻说书人成为曲艺名家的历程,也标志着一种新型讲故事的艺术及其写作—表演主体的诞生。而这种艺术创新的历史地理起源几乎从一开头便显现在作品的肌理中。
田连元当时是本溪市曲艺团的青年评书演员,从属地角度看,《追车回电》是说书人讲述自己城市的故事,但这座城市不是孤立再现的,而是在与其他城市的媒介关系网络中展开自身的叙事:一位本溪老大娘的女儿女婿调到了成都工作,她乘火车去探亲—先直达北京,再从北京转车去成都—在火车快到锦州时,发现写着女儿家地址的信皮忘在家里了,列车长让沿线车站的值班员用铁路专线电话通知本溪站,本溪站的工作人员骑自行车到老大娘家取信皮,再把信皮上的地址通过电话回传给列车将要抵达的下一站,经过若干波折,终于在车到北京之前把地址传递给了老大娘。
本溪是故事起始的地点,也是信息回返和再发出的原点,但《追车回电》地理叙事的起点却在这个原点之前,即本溪之前的始发站丹东。作品的开篇—“从丹东开往北京的快车眼看就要到锦州车站了”,不仅是对主人公搭乘的交通工具的描述,而且是城市的区域地理位置和区域本身的媒介特征的再现。丹东、本溪、锦州分别位于辽宁省的东南、中南、西南,呈斜三角形分布,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是以省会沈阳为交会点的两条铁路—沈丹线和京沈线,城市群和铁路网彼此指涉。
东北铁路网及沿线城市群形成的时间,大致与评书从关内传入东北的过程重合。当代用汉语普通话表演的评书有两大文类派别起源,一是晚清北京评书,一是同一时期流行于河北的西河鼓书,两派艺人自清末至民国大规模流入东北,是以铁路为媒介的移民潮的一部分。以后来的“评书四大家”—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和刘兰芳—为例,其中三人在东北的早期经历都展现着上述流动的媒介特征。出身西河鼓书世家的田连元籍贯为河北盐山,出生在长春(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分界,东北铁路系统的南北枢纽),最早有记忆的地方是四平(南满铁路和四洮线、四梅线的交会点)。同出西河门的单田芳生于天津,最初记事时生活在齐齐哈尔,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随父母在东北城市间来回搬家的路线—从齐齐哈尔到吉林(市),南下沈阳,又北上折向长春,恰好指涉东北铁路史的不同脉络:晚清政府的自建铁路(齐昂铁路)、沙皇俄国修建的铁路(中东铁路)、晚清政府向日本借款修建的铁路(吉长铁路)、奉系军阀的自建铁路(沈海—吉海铁路)、在俄日殖民者之间易手的铁路(南满铁路)。四十年代中后期,当一九三四年出生的单田芳、一九四一年出生的田连元还在随流动说书的父辈迁徙时,一九二九年出生的袁阔成已作为北京评书“袁氏三杰”的传人在沈阳独立登台,随后沿平沈铁路(其间曾因战时火车中断而改换马车)逐城献艺:新民、锦州、山海关、秦皇岛、唐山……其轨迹反向展现着评书北传的交通地理。但另一方面,在流动说书卖艺的时代,说书人一旦走出火车站,进入茶社或书场,传统文化空间便割断了其文化主体的流动经验,换言之,评书借以传播的区域媒介地理长期被排除在说书人的“书”外。
当代媒介经验成为评书艺术生产的有机构成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前提的。根据单田芳的解释,传统说书人的普遍流動卖艺与其故事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一个说书人一生只会说一部书或几部书,不可能对着一个地方的听众反复讲,“所以必须流动到其他的地方去说书”。在师徒口耳相传的生产方式下,说书人一般只能讲从师门聆受的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