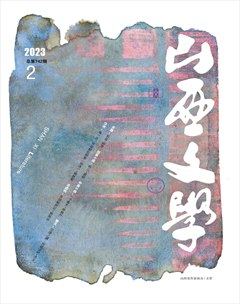麻子的太太童文卿在将军九爷的陪伴下,回老家那日穿的即是一身旗袍。
好凑热闹的风先生,遇着这样的稀罕事儿,岂有不紧跟的道理。他开心快乐地跟在麻子太太和将军九爷的身后,笑靥如花,别人不晓得麻子太太裹在身上的衣服叫旗袍,但他是知道的,知道那时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开化早的地方,时髦的女子,都会穿旗袍。相对落伍的古周原上,乡亲们也许听说过,但绝对还没有见识过。所以在将军九爷扶持着麻子太太童文卿走来时,冯家村的人,一街两行,张嘴瞪眼睛地看着她娉娉袅袅一路走来,没有谁能说出一句话来,便是平日里扯着嗓子高叫的鸡,这一日日怪得也不叫了,便是平日里吠声冲天的狗,这一日亦日怪得不叫了,村子里静悄悄的,有种窒息的气氛。
本来是,做了太太的童文卿是坐着一辆马拉轿车的。她坐在舒服的轿车上,能一直走到冯家村她老家的大门口,然后下轿,然后进门,然后威风八面地坐在上房主人的位置上,接受家里家外以及粗作、下人们的拜见。冯九爷的家里养了许多粗作和下人。起早时他因为家贫是没有这些享受的,他拉起了一支队伍,穷家呼啦啦就富了起来,置了百十顷土地,盖了一处三进的大宅院,便雇了许多粗作、下人,还有一班扛枪护院的武装,黑黑明明在冯家村周遭转悠。村子里的人心里也许恨着冯九爷,嘴上却都感恩戴德,说不尽的恭敬话,因为村子里一十三社的青壮年,一些人跟到冯九爷的队伍上发财去了,盼望一日也能如冯九爷一般威风;一些人则租种着冯九爷的田地,糊着他们饥饿的嘴……对于老家的这些情况,做了太太的童文卿从九爷嘴里耳闻到了。不过她心里有自己的主张,金陵女子大学的高材生,有着满脑子的民主思想,她压根不想,也不愿意在老家耍威风、显贵气,马拉轿车走到离村一里多的地方,她招呼驾轿人停下来,自己掀开轿帘,身轻似燕一般,从轿身里落到地上。
古周原四月天,在风先生眼里花红柳绿,春风漫卷着的油菜花儿,黄亮亮地夹在绿汪汪连天接地的麦田里,不仅使风先生感到眼晕,便是下了轿车的麻子太太童文卿,一时也眩晕得厉害,采花的蜜蜂,翻飞的蝴蝶,都是那么勤劳,飞来飞去,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穿着旗袍的麻子太太,揉了揉眼睛,再睁开来时,当下就喜欢上了她初次踏上的老家景色。她的脸上因此荡漾着如油菜花儿一样灿烂的笑容,向着绿树婆娑的冯家村,兴致很高地走着……风先生知道,童文卿这么做是拗了冯九爷的意的。冯九爷想要让她耍耍威风,摆摆阔气的,可她有她的一套道理,劝冯九爷说了,面对家乡父老,咱要低调,咱要谦谨,咱要恭敬。
冯九爷虽然是位受人敬畏的将军,却也是个野人,很少能听进别人的话,麻子太太的童文卿张嘴说了,他就不能不听,而且是有一句听一句,有一声听一声。
冯九爷就服他的太太童文卿。她既下了轿车,他还能骑马吗?当然不能,因此他也就下了高头大马,让童文卿一手挽了他,恩爱双双地走进了冯家村……初次走进村子的童文卿,穿的是件黑色真丝织锦缎面料的旗袍,裁剪合体的旗袍把她的身条裹得紧绷绷的,该凸的凸起来,该收的收进去,从细白的颈脖上起头,有条红色的弧线,自胸前自然地划过,像是一颗流星,划在寂寞的黑色里,就只是一瞬间,亮了一下,重新归于黑色的沉郁。有菊花的盘扣,沿着那红色的弧线,均匀地铺陈开来,绽放着犹如星星一样的闪光。还有一只同色丝线绣制的凤凰,鲜活在她旗袍黑色的面子上。麻子太太有款有型的走动,一街两行的鄉亲们,特别是如她一样的女人,蓦然就都生出一种枉活一世的自卑,在心头针扎一样痛着!童文卿不知乡亲们的心理活动,她礼貌周全地对着街上的乡亲,慈爱地笑着,不断地点着头。但她的礼貌和周全,还有慈爱,并没有引起乡亲们的回应,她眼睛看向谁,谁就会低下眉目,不看她,也不问候她。不过他们会要问候冯九爷的,怯生生你方问罢他又问,大家的问候声不绝于耳。
童文卿心里就起了疑,不晓得乡亲们那日咋就不搭理她呢?不过,她看得又极明白,乡亲们虽然不搭理她,但最感兴趣的却还是她,风先生于日后民间的传说中,给她做着证明。
只说童文卿那日穿的旗袍,黑色真丝织锦缎的底子,日后在乡亲们的回忆中,没有争议。但底色上的开襟,开襟上的绲边,绲边上的盘扣,以及黑色面料上的花样,争议便十分的大,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说法,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说法。只说那盘扣,就有说成蜻蜓扣、青蛙扣、蜜蜂扣、蝴蝶扣、燕子扣的;就有说成琵琶扣、琴瑶扣、花蕾扣、纽丝扣的;就有说成菊花扣、兰花扣、桃花扣、木棉花扣的等等,还有黑色旗袍上的那只凤凰,亦多有论说。总之一味地传说着,不知还会传说出多少新花样来。但有一样东西却众口一词,几无争辩,那就是对麻子太太的评价了。
乡亲们说的是:麻子太太的童文卿也太那个了。
乡亲们说的是:她和咱们不一样,不是一点不一样,是太不一样了!
从乡亲一口一个不一样的叙述中,我的阅历浅,听不出来,但风先生的阅历丰厚,他听出来了。听出了大家对童文卿的羡慕,也听出了妒忌,还有丝丝缕缕的仇恨。风先生虽然听出了这些不甚友好的感受,却也并不气恼,而为有此议论的童文卿,还要生发出一种她才有的孤高和骄傲。
风先生因之要说了呢,他说:众口对一个人的敬畏,有时还就是从羡慕、嫉妒、仇恨开始的哩。
风先生说:人所有的作为,都是自己的选择,唯有自己可以诠释。
麻子太太的童文卿挽着冯九爷的胳膊,回到冯家村的日子不久,冯九爷便千不舍、万不愿地离家走了。身为国军将领的冯九爷自有军务缠身,他不能在家里多待,他要振作精神奔赴抗击日寇的前线上去,杀敌报国。临行时,九爷放心不下他年轻漂亮的太太童文卿,就问了她一个问题。
冯九爷说:我走后你如何自处呀?
童文卿对他嫣然一笑说:放心不下我吗?那好,你别打鬼子去了。
冯九爷听她这么说来,当下便急得红头赤脸。他说:我不去打鬼子,哪里来的你嘛。
童文卿说:你说的倒是实情。那你说咋办好呢?
冯九爷说:我说不好,你说吧。
童文卿就把她在心里想着的一件事情说给九爷听了。她说:我办一所学校如何?
童文卿说:东北、华北流亡的青年学生太多咧。他们没处去,我办学收留他们来,继续他们的学业,让他们给你将军九爷扬名号!
冯九爷朗声地笑了,他鼓励太太童文卿说:咱家的地亩够你用了吧。
童文卿当着众人的面,偎到冯九爷的怀里,仰起脸儿,把她热烘烘的嘴巴,在九爷胡子拉碴的脸腮上,亲了一口,转身进入家门里,翻出她曾穿给将军九爷的那袭血色一般的旗袍,一手拿着琵琶,一手拿着单人坐的凳子,就又走出大门来,很是雅致地坐在凳子上,怀抱着的琵琶,顿然给九爷弹拨起来了……不知将军九爷听得懂听不懂童文卿弹拨的琵琶曲,但风先生是听懂了,他听似《诗经·清人》弹拨哩。因为此,风先生就还把远古的歌谣,配合着童文卿弹拨着的琵琶曲,大声地诵念了出来: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
风先生诵念着还凑近冯九爷的耳边,给他说了这首歌谣的大意。他说:“清邑的军队驻在彭,驷马披甲好威风。”又说,“两矛装饰重璎珞,黄河边上自逍遥。”还说,“清邑军队驻在消,左转身子右拔刀,决战沙场逞英豪”……骑在枣红色大马背上的将军九爷,在风先生的耳语里拨转马头,于童文卿弹拨的琵琶曲里,向着冯家村外跑了去!
此后的一段时间,童文卿脱下她经常裹着身上的旗袍,穿上一身黑色的裤子和袄儿,去了冯九爷留给她的地亩里去,用她金陵女子大学土木工程学高材生所有的能力,酝酿规划出了一所她要建设的学校样子,延揽来的工匠和普通工人,这便大刀阔斧、热火朝天地施工起来了。
童文卿不知道在她全力以赴建设学校的时候,有个叫格蕾蒂斯·艾维德的英籍小女子,带着一百多名年龄尚小的孤儿,冒着日本鬼子的炮火,正从山西省的阳城县,往大后方的陕西省转移了……英国籍小女子的确是小,她的身高站起来比一张桌子高不了多少。童文卿可以不知道她,但风先生是知道的。他在童文卿把新建着的学校差不多建成出样子来时,就往黄河那边的山西省跑了去。他目睹了侵略成性的日本鬼子,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分出一路沿长城而来,进入到山西境内,占据了太原城后,出动他们的轰炸机,向阳城县扑了来,把挂在肚子下的航空弹,一股脑儿往县城丢,其中的一颗就落在了孤儿院的院子里,炸开了花!主持着这家孤儿院的人,就是艾维德,鬼子的航空弹把孤儿院的房子炸塌下来,艾维德和她的孤儿们,全都压在了废墟里。但侥幸的是,除了艾维德的左肩受到一个碎片的伤害外,她的孤儿们都还好,无非这里擦伤点儿皮,那里擦伤点儿肉,筋筋骨骨都无大碍。
轰炸过后,艾维德先从废墟里爬出来,她在闻讯赶来的乡民们帮助下,把廢墟里的孤儿们,一个一个地扒拉出来,让他们站好队报数儿,报到一百零三这个数字时,艾维德软在了地上,她哭了……风先生就在这个时候,如一阵风似的赶到了艾维德的身边,他不仅看见艾维德左肩上流着血,还听见软在地上的她,哭泣着不无愁烦地说了。
哭泣着的艾维德说:好啊!一个都没少。
哭泣着叫了一声好,说了一句话的艾维德紧跟着还说:可恨的日本鬼子呀!你让我和我的孤儿们怎么办呢?
风先生插话进来给艾维德说了。他说:走,只能走。
风先生说:跨过黄河,往陕西那边去。那里有个你一样的女子,名叫童文卿,她能收留你和你的孤儿们。
正如风先生说的,艾维德与她的孤儿们离开阳城县是一个必然。英国籍的小女子艾维德,生来遇到的事,无一不艰难。她从母国来中国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的她,在伦敦的一位教授家里做客厅侍女,出身贫寒的她,没有读过书,但她在教授的身边,耳濡目染,不仅识得了字,还学习了许多文化知识。很偶然的,教授问了她一句话,说你想出国吗?她点头了。教授便给她讲了中国,讲了他在中国的一位姑姑,年岁大了,想要返回母国来,但她在中国还有割舍不下的事情,需要有人接班,继续她未竟的事情。艾维德听教授这一说,她没有犹豫,答应了教授,这便离开母国往中国来了。
小女子艾维德是绕道东欧,经西伯利亚来中国的,路途的艰辛与艰难,唯有经历过的她知道,稍有差池,都可能把她的小命丢在路途上。小女子的艾维德好就好着她的小,总能遇到怜悯同情她的人,使她虽然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还是来到了她要到达的阳城县,接过了教授姑姑的班,马不停蹄地便投入到工作中。
艾维德的工作很单纯,就是接手教授姑姑开办在县城里的“六福客栈”,接待往来的骡夫住宿,依此筹措传达福音的经费。有着客厅侍女经历的艾维德,做起这样的事情,轻车熟路,顺风顺水,比她的前任教授姑姑做得还好。几年下来,到了1936年,六福客栈不仅赢得了众多骡夫的青睐,使这里客满为患,生意兴隆,她自己也被包括骡夫在内的阳城县人所包容,让她光光彩彩地加入了中国籍,成了个长着外国人脸的中国女子。
就在这个时期,艾维德用九毛钱收养了一个孩子。
身在阳城县里的艾维德,竟然多管闲事地参与到了“天足运动”中。她现身说法,拿她的天足与她见到的妇女比较,说服着她们,使她们都很乐意学习她,不再缠脚。那个九毛钱收养的孩子,就这么闯进了她的生活。有天清早,她在阳城县的街上一边走路,一边宣传“天足”的好,大说咱妇女不应受那冤枉罪。她就那么热情洋溢地宣传着时,看见路边有个小脚的妇人,给一个病弱的小女孩头发上,插了一棵草,标价两个银圆,要卖了她。宣传“天足”走来的艾维德,看着那个小脚妇人的同时,还看着那个可怜的小女孩,而小女孩被她所吸引,就不眨眼睛地看着她。艾维德是躲不开了,就走过去,与那个小脚妇人讨价还价,把身上仅有的九毛钱全掏出来,放在那个妇人的手心里,而后就领着瘦弱的小女孩,一步一回头地去了她的六福客栈。
小女孩没有名字,别人叫她“九毛”,她坚决反对。艾维德想了又想,她给她想了个“美恩”的名字。
六福客栈的老板艾维德先有了一个女孩美恩后,接着又有了男孩“少少”和 “宝宝”……艾维德收养的小孩子愈来愈多,到后来,她用她六福客栈的收益,在阳城县创办起了一个孤儿院,她因此就也成了阳城县里的大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