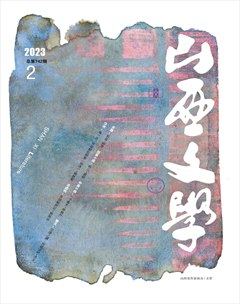村落
村子在县城西北,傍着汾河,西行的主干道从村子的心脏上呼啸而过,为它输送新的血液和养料,如果再加上二十一世纪中现代文明哗然的蒸腾,这里便如同烤箱中的面包一样,迅速地迭变,膨胀。
在汾河还被奉为神明的历史中,村庄是谦卑的、安谧的。农人的耕耘、制香人的作坊,全赖河水的恩赐,人们不惜耗费工力,在土地上挖出一条豁口,让河水能更深入地滋润这片土地的肌体。现代科技到来的前夜,人们尚且泛舟河上,带着一壶老醋,划向十里之外的村庄,去探望黄土墙下抽着旱烟的老舅。村中古庙中拆卸下的梁木,纷纷投入这南行的河流,向着市中的学府,装点七八十年代一方学子的象牙塔。
现代文明的横行注定需要先驯服那条邻着的河,一点一点与它缠斗,悄悄地侵占它的躯干,让它虚弱,由它枯槁,然后囚禁它,圈养它,让这“洪水猛兽”成为安澜平静的萌宠,穿着人们精心设计的草皮与花树,点缀着彩色的荧光,孱弱如美人。然后彻底忘记它是共工的后裔,曾经冲天奔地,肆虐九州,让大禹为之头痛,汉武为之畅醉。
孱弱相对的是村庄的雄壮和现代文明的强悍。这是一个生产力裂变的时代,人们不必再死守着土地,向老天讨要一年的米粮。工业入驻将会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人们簇拥着厂房,朝八晚六地生活,流水线上的香、机床上的零件、温室之中的菌菇或者厂房之中的香醋,都会通过公路运输出去,最终走向市场,换取村人们的生计。生计之余,人们开始打扮着村庄,小区代替平房,公路代替土路,人们种起了行道树,立起了路灯,此时村庄已经褪去了蓬头垢面,精心妆成了城市。
领略了大部分村落,太多的整齐划一,总让我想起在水泥地之下覆盖的莽原。但现代文明铺天盖地,铺陈出幅员辽阔的同质的土壤,迅速被人們捏塑着,成为示范、样本,直至城市成为森林。
村中的人向我描绘了村中制香的历史,从陕西迁来的一户人家,在寺庙成群的村子中落户,从此家家户户以制香为生计,洪洞一带的香火灯烛,大多来源于此。
香火延伸的是土地上的信仰,在我去不了的历史中,我曾多少次想象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景,这一刻,仿佛就在这土层之下。一望无垠的寺庙楼阁,连着汾河水岸,鹳鸟高旋。人们从岸边挑了水,在凉棚下和着木屑,抽成长条,再剪裁成细香。翌日,妇人将晾干的香取下,捆成把,由丈夫挑着担子,赶在第一缕阳光缀上燕翼之时,在寺庙前叫卖。
“卖香嘞——供奉神佛菩萨的高香——”
与吆喝声一同在时空中氤氲的是烟雾的缭绕,如果有能够洞察古今的延时摄像,那么这烟气必然是慢慢地弥散,那些曾经的庙宇:水神庙、老爷庙、奶奶庙、三官庙、土地庙、玉皇庙、圣王庙、原君庙,从香火鼎盛到无人问津,再到最后,镜头前只留下凋落的庙宇,慢慢荒圮,成为废墟。
村中仅剩下两家世代制香的作坊,也双双摒弃了传统的手工制香,超越于历史上一村垄断洪洞香业的盛况,今时只需一家便能应对市场需求,多余的产能远销他乡。村中的人,走进了学校工厂,也有外出远行的人。在工作时间,街道空落落的,安稳,雅致。
村中尚有一二与历史较劲的人,他们在村落之中,修葺了寺庙,在门口浅浅看了一眼,这里供奉了佛道儒三教众神,似乎有心将那些被人所遗忘的神祇一处安放,为村庄修补一段远古的记忆。也有缝合文字的人,历经三年,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结成一本村志。
觥筹交错间,修志人隐约地提了一句,要让村志成为子孙后代铭记历史的工具书。便仔细问了村中的家族情况是否有记载,修史人说村中几大家族、零星散姓,应有尽有,想到修志人东家跑西家问的口舌功夫,油然地生出佩服和敬仰。
发展并不一定需要遗忘所有。又或许,社会的温度并不在于文明发酵的程度,不管是传统或者现代,一个村庄的温度最终还是人心的黏合。在香厂,我看见张贴着一张招聘50岁到60岁老年人的启事。在中学,办学人斥巨资为学生打造了省内一流的塑胶跑道,在村委会中,有一份记载翔实的留守儿童档案。在寺庙戏台下,簇拥八仙桌老人在曦阳下做着活计……在文明迭变所弥生的缝隙之中,是人心愈合着文明的伤口。
啊!在现代村落的肌体之中,涌动的,终究是人!
出离
从热闹中出离,模糊的喧闹与寥落的心迹生出了一种唐人的意趣——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村中的路弯弯曲曲向天空延展,尽头是砖红色的门楼,一边临着山崖,一边依着庙宇。灯光明明暗暗,又多情悱恻,如同班婕妤孤身在宫闱中挑动的红烛。
灵魂相对时,我想此时我与村庄都有些尴尬。她拒绝着我一切的触碰,街道上闲散溜达的鸡鸭惧怕我的热切,蹴跃过院外的篱笆墙。猪圈中的母猪惧怕我的探究,用身躯掩住崽子的视线。瘫在麦粒上的野猫不肯让我抚摸,蹿进了文化栏旁的车轮下。路旁散发清香的幽兰,埋首灌木丛,不肯接纳我的仰慕和笑靥。
可谁能阻挡醉酒之人的告白呢?我对着她的背影,拉扯了一顿陈年的闲话。我说很多年前,我的母亲已经帮我拒绝了泥土,他们将我裹在城市的玻璃房中,透过电视,我学着去用流行的音乐和彩色的画笔去歌颂城市和工业。他们说土地是粗鄙的,我们要无限地走出去,让外埠的阳光为自己换个筋骨,然后驱使着摆臂机械,高高在上地划破土壤。
我说自己现在是个“光鲜亮丽”的打工者,用着三十岁的精力和颜色来讨好俗世盛赞的功名和安适。把自己活成一把电钻,听从一些所谓“流行”的指挥,不顾一切用力,永不停歇做功,跳跃着触碰那些俗世的功利奖赏,但所得很少。
我说我被城市和文明钳制着,心里还暗藏一片原野,她春时澹冶如笑,夏日苍翠如滴,秋妆明净,冬睡惨淡,娇羞与嗔怒时有薄荷味的柔风。它曾醉倒在我的画卷前,披一身落花,睡梦中说要赠予我四时明媚,像春泉,夏山,秋叶和冬云。
村庄升起了凉风,她柔柔地落在我的肩上。
某一刻,我想我被诱惑和劝解。她说不必仿照文明的规整,且去追随自由肆意的灵魂。院子里可以疯跑着蔬菜和爬蔓,道路上仰卧着车辙和麦粒,小卖部也可以是邮局和茶水铺,屠夫的别院中滚着热辣的羊汤。她说皮囊污浊,定义沉重,地图无效,不必把自己摆在那一种框架中,耕地的是农民也可以是教师;敲大锣的可以是隔壁的大婶也可以是从城市回来的露丝。不必努力去钻研,浪费人生在某一种不实用的方向上。只需坦诚地照顾好自己的吃喝拉撒,然后开怀地笑。
我想我应该犹疑和确认。风混杂了麦田、羊粪、藤蔓和炊烟,我埋首在村庄的血管中,放纵,恣意,啃食,口器未深入肌理,啮咬不到肌肉,热切且不得方向,如同探入的针头、吸血的蜱虫、拖着脐带的巨婴、入侵而来的异生物。我充满了窥探的欲望,想敲破高墙深挖根基探明它的来龙去脉,汲取她魂中的真谛,真切我不明的渴慕。
疯狂,无礼,又或许有些放纵。她只是转身,将灯火点亮,让我看清归途。
路已经走到尽头,那复式的小院比远处的寺庙更显暖融。灯光刺向我的眼,用俗世的“亲厚”刺向我心生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