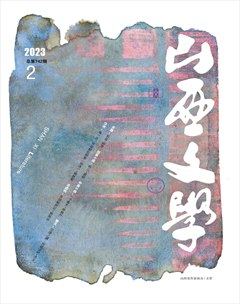编者:“自从我开始写诗以来,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写作进行的,我想象不出不写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您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您是个有紧迫感与饥饿感的诗人,所以您的勤奋有目共睹。那么,您会刻意去训练自己的写作吗?又是如何强化自己的?无论是回望还是期冀,无论是困惑还是喜悦,谈谈您的写作脉络与追求吧。
杨铁军:从大学开始写诗不久,我就有反对趣味的志向,对一切文人趣味和习气保持警惕,和朋友互相勉励,不要玩物丧志,不要沉溺于自身或者任何外部的对象。这种自我要求从一开始的自觉意识,逐渐演变成一种“峻刻”的内在需求,最后也许成了一种自我束缚了吧。
到了最近一些年,我对此有所反思,甚至半开玩笑地和朋友们说,要是从年轻的时候就练练字,甚至搞搞收藏就好了,培养一些“无聊”的趣味,以遣“有聊”之人生。但我的追求已经是“骰子一掷”,虽然还不知道结果,对自己来说,尚有可为之处,但在“上帝”的眼里,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大学时候住六人宿舍,几乎每天晚上熄灯之后,我都点上蜡烛,手里握着笔,眼前是一张白纸,似乎诗句随时就会降临,必须记录下来。但往往好几天,甚至几个月,都一无所获。我聆听到的声音太不可靠,完全不在我的把握之中。所以,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生怕自己错过。一旦把握到了,写下来,如果成立的话,往往都是在一种出神状态下的偶然,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认识能力。现在看来,那些诗并没有什么不能把握的东西,但也确有一种现在的我写不出的味道。
这种焦虑一直伴随着我,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好几年都没写什么东西,觉得自己完了。但是最后也都走了出来。大约2008年的时候吧,这种焦虑有所缓解,我觉得自己肯定还可以写下去,慢慢地,这种焦虑成了隐痛,躲在角落里,继续给我压迫,但是我在写作中已经获得了某种免于焦虑的“自由”。
编者:我注意到,生命的意识或者历史的主题,在您的诗歌中频繁出现。也看到您擅长从错综而无垠的时空中,不断打捞那个微小的“个人”。那么,您如何看待时空之于您个人写作的影响?在不停地迁徙中,写作因而也发生了什么?
杨铁军:我的诗是从一颗种子、一朵花开始的,我最早的诗之一,就是关于一朵蔷薇,开头两句是:
“你这朵独自开放的蔷薇,
难道不知你只嗅到自己的芳香?”
结尾是:
“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撑起一朵蔷薇,
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块孤独的内核。”
我以为我这些年来已经开阔太多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还是时时都落脚于这个原初的开端。
我不信任“趣味”,更不信任“宏大叙事”,大多数浮于表面的那些东西,在我看来都很可疑。一个诉诸方便法门,向着既有思维的套路上去靠拢,而得来的诗学,对我来说,不啻偷懒取巧,是我做不来的。但是时下这种诗,说实话,特别多。
我始终觉得个人的感悟和经验是一个诗人最坚实的基础。不要绕圈子,应该当下得来,不要“直把杭州作汴州”。当然,我也并不是没有另一个角度上的自觉,所以我的那个“我”好像总是处于一个历史中,是一个快要崩塌的、需要赎救的形象,这个也许就是我的问题意识吧。
编者:在异国他乡那么多年,想必有太多点点滴滴,仍会如烟霞萦绕,仍会如孤鹰盘旋。对您而言,那段往事是什么?它对您如今、以后、一生的写作,会有怎样的触动、消弭、改变?
杨铁军:我是1995年去美国上学的,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