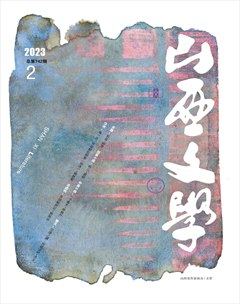自驾驱车近千公里,头天晚上八点钟到北京,第二天清晨九点,我要在京郊农村租间房子。
已经是南六环,就到北京西南真正的城乡交界处了,女儿还继续往南走。身旁,新修的八车道大路光鲜亮丽,让人误以为还在城里。背后不远处,是个叫作地铁站的地方。北京的地铁进入郊区,就从地下冒出来,在高高架起的轨道上奔驰,地铁就变成了城市轨道交通,简称城轨或轻轨,这名字怪怪的,除了工作人员,大概没人这么叫。地铁站前,是一条上下六车道公路,在我的印象中,那里的车辆似乎从来都塞得严严实实,几年来就没有动过。道路两旁,新建成的高档小区里,乳白色的别墅和同样乳白色的高层住宅楼相間,气宇轩昂,高贵得让人自卑。两三年间,房价已从两三万一平米,飙升到五六万。再往南走,城市味道渐渐消失,先是圈起来的地,一片连一片,成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缓冲带,绿色的铁网已有锈迹,多处被撕开了口子。从我第一次来这里到现在,已过去五年,还一直圈着,不动工,也不拆除,其中杂树疯长,荒草萋萋。每天不等入夜,道路两旁的路灯就亮了,一片通明,照出的分明是一个华丽光鲜的世界。
继续往南走,一座村庄挡在十字路口,路面骤然变窄,路口两侧也是一条东西向的现代化街道,若城市与乡村的分界线,划得浓墨重彩。路口南边突然缩为灰头土脸的二车道乡间公路,气势如虹的城市像被卡在村口,憋得面红耳赤,动弹不得。又感觉无与伦比的城市扩张,硬生生从平静的村庄劈出一道缝,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道缝隙在不断扩大。
沿这道缝隙往里走,就从城市进入乡村,尽管之前有连片的街道和空地过渡,转换得还是太突兀,让人猝不及防。路两边是简陋的小店铺,以前数过,分别有小饭店十三家,理发店五家,还有号称超市,实际是小杂货铺的商店七八家。让我感到亲切的,是小饭店中有一家山西面馆,老板的村子与我老家村子距离只有二十里。店铺都只有大门,没有门前,出了大门,就是各种车辆川流不息的公路,各家都把地方利用到极致,门外别说停车,就是站个人也惊心动魄。最骇人的是渣土车和工程车,吼叫着霸道的声音,喷出黑烟,带起尘土,经过时,各家小店都浑身战栗,好像胆小怕事的人,捂了耳朵往一旁躲。路东商店后面是一条铁路,由北至南纵贯全村,在房舍间时隐时现,亮晃晃的,利刃般将村舍划开一道豁口,不过,从没有看见过一趟列车经过。
人也变了,抬眼所见,到处是衣饰不讲究的农民和农民工,虽然还是京腔,却是粗声大气,偶尔看见衣着讲究的俊男靓女,反而感觉与周围环境不协调。
这是个已经被城市扩张震惊得跳了好几跳的村庄。北京城已踅摸到了村口,渗透到街面,踅摸到每一个村民心里。这几年,我每次来,都能看到窄窄的道路两旁在紧张施工,许多房子已经长高,还有些房子正在长高,一家一户不大的宅基地全都筑起了楼房,像别墅,更像堡垒。升降机、吊车和水泥罐车将村子搅动得惶惶不安,明明就停在自家门前,却将路堵上了,因为自家门前就是公路。两边的汽车排出了村,委屈地鸣叫,不安分地往前插。不过,道路再堵也没人去管,更没有人为过往的行人担忧。在这里,房子才是老大,建房是天下最理直气壮的事,任何事情都要给建房子让路,堵就堵上一会儿吧。
与别处的房子不同,这里的房子都显得心事重重。不管正在施工的新房子,还是破败的老房子,好像都长着一双贼亮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北边的都市。前几年我初来时,房子都像村巷里的老农,噙一管烟袋,无奈地蹲在墙角,看行人往来。这次来,明显地感觉到,所有房子都站了起来,神色慌乱,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朝远处张望。
城市建设已逼到村口,村庄心烦意乱,六神无主了。
我不需要这种地方的房子,从千里外的晋南来到京郊,我租房的标准有二,一是安静,二是便宜。远一点,条件差一点,位置偏僻,一点关系都没有。
与车水马龙的纵向公路相连的,是七八条横向村巷。要租到安静而又便宜的房子,就得往里走。选一条较宽的巷子走进去,才几十步,隆隆车声没有了,村庄平静了。九月的京郊天色湛蓝,没有风,八九点时分,该上班的都上了,该上学的也上了,巷里很安静。一位穿暗红马褂的老妇人,守着一辆绿色三轮柜车,用很大的幅度扫地,刺哗刺哗响。见我和女儿过来,停下来望。巷道一侧有几家庭院改造的公寓,进去问,说是一千元一月,房子大概有十几平米,带卫生间,我想要的就是这种房子,不想已租完。出来后,扫地的红马褂老太太眼睛就亮了,问我们是不是要租房子。我说是。老太太说:这里的房子都贵,跟我走,有便宜的。我说太感谢了。看老太太红马褂上印的字,知道她是村里的保洁工,可能负责这一段道路的清洁卫生。老太太古道热肠,素不相识,为给我找房子,地也不扫了,推起三轮车,往村里走,说自打地铁修过来,村里租房的人多了,租金蹭蹭往上蹿,不过,村里和村口租金差几倍,只要两三百元就能租到一间。拐过几道弯,进入另一条巷子了,再走几步,已经从村东走到村西,眼看就要出村,进入一户人家。户主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见有人来租房,并无多大热情,没一句话,领我们进入东房。上首是五间北房,可能是房东一家人住的。与东房相对的西房,已租出去。房间里空荡荡,还算干净。问什么价格,说是三百元一间,共三间,要一起租出去。
说话间,我猜房主心理。这三间东厢房,在院子里位置最不好,进深不大,最多四米吧,开间也不宽,三米多,说是三间,其实也就三十多平米。因而,要论间而不论面积。我说:我租房子的目的,是要给自己找一个空间,读书写作,并不需要这么大。老太太说:那再去一家,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村里空房多着呐。
沿着巷子七折八拐,又一阵兜转,从村北走到村南,一路走,各家院里的狗隔着大门一路吼叫,音色不同,都好像马上就冲出来。还有两家的狗站在楼顶,头顶蓝天,居高临下,叫得威风八面。虽然远离家乡,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行走,我感到一切都是熟悉的,贴着门神的大门,吊着灯笼的门楼,门前高高的台阶、院墙内的绿树,转弯处的几蔓丝瓜,还有从门洞下钻出的小猫。这一切,与晋南乡村几无二致。只是巷道都不宽,各家都寸土必争,哪怕一小块犄角旮旯,能砌到墙内,绝不留在墙外。走一段,就能看见有人家施工,都是小打小闹,三五个工人而已。老太太不时停下和人打招呼,有时,感觉周围没一个人,却见老太太热情满怀地说笑,往上看,有人站在墙头砌砖。
穿过一条甬道般的窄巷,来到一片较宽敞的地方,几个人正在打水泥地,听口音都是外地人。再拐进一个红砖墙围起来的场院,里面有三家人,迎面是个大门紧锁的小院,西面又是一条窄窄的巷道,拐进去,可见两座刷成灰色的砖门楼,都朝东,走到靠北一家,老太太说:就是这里。身后,墙角下是低矮的狗窝,一只形体巨大的黑色土狗伸长了脖子,从我们刚进来就一跳一蹦,将铁链扯得哗哗响,狂吠。老太太呵斥,黑狗呜咽两声,委屈地卧下。这家大门同样紧锁,老太太说:下地了,不要紧,我知道钥匙在哪?说完,在大门右侧的一堆乱砖下翻,果真找到一把钥匙。老太太很得意,我也感叹,看来这种藏钥匙方法,全国农村通用,我小时候,妈就用过这种方法。现在,妻子还用这方法。就在昨天早上,我来北京之前,刚刚才将藏在大门口隐秘处的钥匙收拾了。显然,这家人藏钥匙的目的与我家不一样,我们家藏钥匙,是因为将钥匙锁在家里两次,头一次,由住在同一条巷的派出所民警搭梯子翻进家里取出来,我并没有汲取教训,只是记住了警察的好。没过几天,又将钥匙忘在家里,这次,那位民警不在,只好自己搭了梯子,爬进家里取。后来,就想起了这个古老的办法,弄一把钥匙,藏在门前自以为隐秘的地方。
打开门,门洞里放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车厢里有镢头和铁锹,靠墙放几袋复合肥。院子不算大,四分多的样子,有北房和东西厢房,南边是前面人家的北房。整体格局和刚看过的那家差不多,都是京郊最普通的农家。正是秋收季节,院子向阳处,摊满了花生,墙上靠着密密麻麻的芝麻秆。老太太说:这家孩子进城住楼房了,家里就老两口。仔细看,房子都是标准的京郊农村式样,起架不高,窗户很大,砖木结构,房顶却没有瓦,用水泥抹成坡状,圆滚滚的。京津冀乡村常见这种房子,一般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
那个年代,是建国后全国乡村第一次建房热,刚刚因改革开放有了点钱的农民,填饱了肚子后,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建起一座新房。因为急迫,又因为囊中羞涩,那一茬的房子质量普遍都不高,材料能省则省,钱能少花尽量少花。同时,那又是中国北方乡村建筑史上,第一次告别土坯砖木混构,迎来青砖水泥房的时代。看到这样的房子,虽未谋面,我已能判断出房东的大概年龄。因为,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同样身处乡村,同样在那个时代为自己建起了房子。
要看的是西厢房,打开门进去,里面空荡荡,水泥地面有些地方开裂翘起,白色墙壁还算整洁,整个屋间只有一个立柜,黄颜色,简朴结实略显粗笨。是伴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房潮打的家具。我在房间走了两步,立刻闻出有种怪味,潮潮的,似木料发朽,是那个年代的味道。房子共两间,二十多平方米。南面还有一间,单独开门。老太太说已租出去了,去看了看,里面堆满东西,因为紧挨着前面人家的房子,阴暗潮湿,不适合居住。
再从院里看这两间房子,八九点钟的阳光照在窗棂上,明光灿亮。窗户下面围靠的芝麻秆,铁丝上挂的衣裳,院外枣树上的鸟叫声,将房子陪衬出满满的田园风情。
我和女儿对这房子还算满意,主人不在,老太太說:中午一点半,你们再来,到时候家里就有人了。
吃完中午饭,正好是约定的时间。再去,大门果然洞开,走进去,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在收拾院里的花生。见我们来,站起身,脸上的皱纹瞬间开出了花。这就是房东太太,个头不高,最多一米五,强壮结实,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绾个髻。脸晒成赤红色,赤脚穿一双塑料拖鞋,一看就是常年在田里干农活的。我说我租房子,晚上却不住,也不开火做饭,只是白天过来读读书,写写字。房东太太说,那敢情好,我这院里,白天也没人,老头给人打工,我下地,安静得很。我问:有没有桌椅和床铺。房东太太说:都有,你要住,下午就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