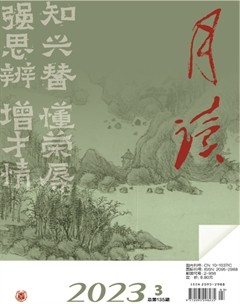郑板桥(1693—1765),本名郑燮,江苏兴化人。他功名顺利,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不过仕途未称其望,只做过山东范县、潍县等地县令。辞职返乡,鬻字画为生,是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有诗、书、画三绝之誉,其“笔墨”超群,为人亦卓绝,时有“真气真意真趣”的“三真”美称,其立身行事,常迥乎其世,有“非人非佛亦非妖”的“顽仙”之喻,留下了很多令人感慨也耐人寻味的故事和主张。比如对小偷,他虽也认为“窃贼固当执之于法”,但在其家书中,他却坚称“盗贼亦穷民耳”,一再要求家人善待、宽容他们;其间恻隐的温情溢出人性的暖意,而其间豁达的同情则透出别致的况味。
在他自己所编纂、印行的《板桥家书》中,有三次谈及“盗贼”。
第一次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他告诉堂弟郑墨,想告老后在扬州鹦鹉桥至杏花楼一带,买地盖房,“结茅数间”,“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有几间平房和亭子点缀其间,以与友人谈天说地,论书赏画。宅院没有高大围墙,也没有严实的大门,更没有四角的碉楼,所以其安全性或不足,防不了贼。但板桥让弟弟不必担心,“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此时他还在范县当父母官,信中口吻不无戏谑,却依然流露出对所谓“盗贼”的同情理解:一是身份上,认为贼也是民,不是匪,只是处境窘迫的穷民,信中“开门延入”云云,实视之为客;二是财富可共享,信中的“商量分惠”,以及听其所取,甚至传家之物(“王献之青毡”),亦可任其拿走换钱救急等等,都流露出一种不在意小偷窃己之财的意思。
第二次是在《潍县署中寄四弟墨》一信中,他要求老弟不要追究家中长役郑迁偷盗外逃的行为。郑迁七岁被卖入郑家,但板桥早就悄悄焚毁了他的卖身契,并为他改名,且时加教诲,希望他做个好人。不幸事与愿违,最终郑迁还是伺机偷了约“二十千”米麦,逃之夭夭。郑墨欲告官追捕,但板橋回信劝慰,劝弟弟不必追究了,只是以后雇佣审慎点就可。因为这些受雇之穷苦工役,无钱读书,大都属“乡愚无知”,不知忠义为何物,所以难免犯礼触法;而那些“士大夫知书明道,而清正廉明者尚不多见,何怪臧获之鼠窃狗偷,不识廉耻也”。这一尖锐的对比,实际是在为郑迁一类的家贼开脱,是要求在哀其不幸与不争的视野下,原谅他。
第三次是在《潍县署中谕麟儿》一信中,其子(麟儿)来信告知家中遭贼,正“拟报官追缉”。板桥复信说:如果损失不大,就不必告官了:“窃贼固当执之于法,然彼为饥寒所迫,不得已铤而走险,不偷农户而窃宦家,彼亦知农民积蓄无多,宦家储藏丰富,窃之无损毫末,是即盗亦有道之谓欤?与其农家被窃,宁使我家被窃。”信中希望其子以东汉末陈寔的“度量”为楷模,善待“梁上君子”,甚至可以“善言规诫,并赠金令作小本经营”。较之前面两次,这封信对小偷的态度显然更是友善,既为其开脱(饥寒所迫),又赞其“有道”(不窃农户而窃宦家),还让家人学习陈寔,“赠金”解其困,助其为良。
这三封谈及盗贼的信,都是写在为官的任上,身为朝廷官员的郑板桥,当然明白偷窃违律,应当法办;但在涉及自家遭窃、在和家人讨论如何面对与处置时,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宽恕窃贼。这种怜悯是在家书中流露的,是真挚而诚朴的,并非是出于名士之狂的故作惊世之语以炫世邀名。那么,板桥的宥贼有哪些隐衷,体现了何样的情思呢?仔细品味他的文字,大致能从其心曲中看出一些端倪。
板桥出身贫寒,早年备尝人生艰辛。据其《七歌》所述,他三岁丧母,家中“时缺一升半升米,儿怒饭少相触抵”,看来是常饥肠辘辘。他特别怀念乳母费氏,“每晨起,负燮入市中,以一钱市一饼置燮手,然后治他事。间有鱼飧瓜果,必先食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