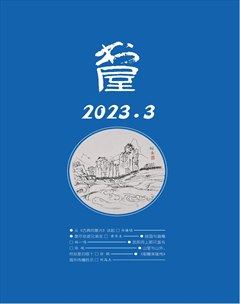易君左(1899—1972),名家钺,字君左,湖南汉寿人,早年考入北京大学,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任安徽大学教授。1932年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主任。抗战期间先后任《民国日报》社长、《时事与政治》月刊社社长。抗战胜利后任《和平日报》上海分社社长。
易君左实际上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因其祖籍湖南汉寿在三国时置龙阳县,人称“龙阳才子”。易君左也是名门之后,其父易顺鼎乃清末著名的大诗人,可谓家学渊源。易君左善诗文,尤善游记,鲁迅先生对其游记作品也多有好评,作品有《易君左诗选》《易君左游记精选》《西子湖边》《江山素描》等,定居台湾后出版了《中国政治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学史》等。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局势紧张,国民政府酝酿迁都,江苏省政府抢先一步将部分机构迁到了与镇江只有一江之隔的扬州。时任编审室主任的易君左随先头部队过了江,临时在扬州中学内办公。
扬州自古不缺文人雅事,易先生的到来又为扬州添了一段文坛闲话。在扬州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易君左像古代所有的文人一样,纵情扬州的山水,据说光平山堂一处就去了二十多次,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诗歌、小品文等。
易君左查阅大量的地方史志和关于扬州的笔记文稿,精心研究了扬州的历史沿革、风物掌故等,又结合几个月来在扬州的见闻,很快就写出了一部四万多字的《闲话扬州》,交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
其实,易君左对扬州的风景颇多誉美之词。扬州的风景是清雅秀丽的,并且充满了历史的痕迹和诗意,但那是属于过去的,是逝去的荣光。近代的扬州毫无疑问衰落了。以上海抑或南京的“现代”作为参照,扬州的确已是烟花落尽。所以,易君左在《扬州人的生活》部分对扬州的市政建设、扬州人的生活习俗进行了批评:“最坏的是路。除开惟一热闹的区域如多子街、辕门桥几处外,无论大街小巷,都是乱石砌成,上无漏水,下无阴沟,下一次大雨,通衢便可行百石之舟。”揚州城的主要交通工具为黄包车,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在扬州也有一辆摩托车,听说是督办公署的,我在南门街上发现过一次,围而观者如堵。”扬州城没有摩登大厦:“在扬州你如果发现有楼房,我出一块钱;发现两层楼,我出两块钱;以此类推。”这最后一句话虽是调侃,却略显轻薄。
还有,扬州城没有卫生系统:“住宅以外的清洁真谈不到。所有灰屑并没有一定的储所,任各户自由的倾积:什么水都向街心泼。无论何处都是小便所,许多土著都在红男绿女过路的草坪中公开的大便。”
如果说以上批评还限于市政建设和卫生状况的话,那么对扬州人生活习俗的批评却得罪了全体扬州人,他说:“扬州有一句最普通的俗语,就是‘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我们可以在每天上午八九点或十点多钟看见扬州人在街上刷牙齿,大概是起床了。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皮包水’!三三五五或独自一人到茶馆儿,坐下,这就生根了!……这样悠悠的灌一肚子水,至少要花费几个结实的钟头。好像是应该回来了!有万不得已的事这才去做做,否则飘飘然的出了茶馆儿,在街上又飘飘的荡一下,就打马到浴室。”“在街上很难遇着一个精神饱满的人,放雀、玩花,是扬州人最高尚的消遣了”,“扬州人的生活象征实在是散漫的很,没精打采的。